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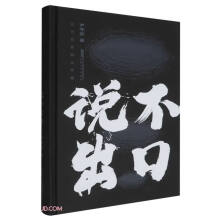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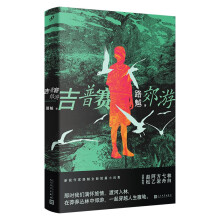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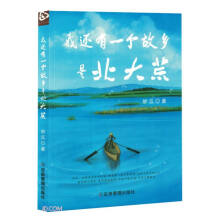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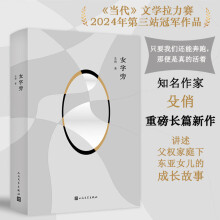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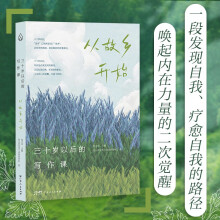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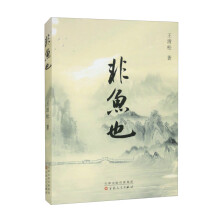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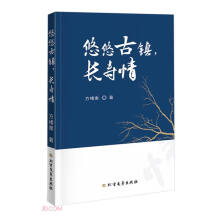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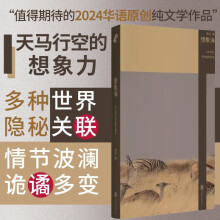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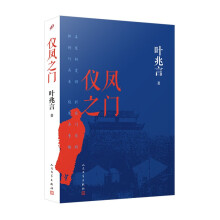
本书所收入的小说多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素材,却以一种高度自由的、超现实的手法加以表现。内容涉及童年回忆、日常观察、社会学思考、科学幻想、古代传奇等。语言灵活多变,叙事充满诗性,往往在极短的篇幅内,提供一个看待周围世界的全新视角。作者以其强大的想象力与精简、清奇的语言风格,向我们展现了当代中文写作的又一新的可能。
12 号楼
垡头,北京深处的一个孟买,街上弥漫着一种边民情绪。一个老太太拿着榨菜闯进超市,吵着要换一袋豆瓣酱,服务员拒绝了她。
结账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现在是春天,我往外看了一眼,突然发现金蝉南里的 12 号楼正在拷贝它自己。
两年前,久石让的秃头倒垂在欢乐谷上空,现在又发现一个楼在静悄悄地、飞快地拷贝它自己的本质,一个又一个,12 号楼堆在 12 号楼里面,看起来就是 12 号楼,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有点惊了。这种从本质到本质的复制,虽然在剧烈地进行着,但没有烟,没有辐射,没有用力的声音,也没有糊味。感官无效,只有一种自然的直接察觉。当我望向 12 号楼的时候,事情就忽然变成已知的了。
一个东西的本质会自行复制,这是常识,是自然法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小学课本上都已经学过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拷贝是原发性的,没什么影响,至少现在为止科学界没发现过什么后果。一般会认为,许多个完全一样的本质重叠在一起,不会更重,也不会更致密,一加一还是等于一。
其实拷贝的后果,就是如今我们的现实世界。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事物的拷贝,和下雨时下雨一样正常,我们经验之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拷贝完成之后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样,无法知道也没有必要去知道。
也有一种看法,说本质拷贝的结果就是增加了解离的可能性。没有拷贝,就不会有解离。
网上也都在猜想,世上所有漫长的痛苦,和无法接受的意外,都源于拷贝带来的小概率情况,比如本质排异或者本质解离。比如湛江船厂的事故,塔斯马尼亚袋狼的消失,还有印度洋上消失的飞机。甚至李约的感冒,很可能都有同一类简单的原因,只是无法证实。
楼房这种东西人们很熟,它们很稳定,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早就拷贝完毕了。都是沉重的一个,发出听不见的蜂鸣,有着渺茫的引力,不知道是由三个还是几千个它自己叠在一起。
让我吃惊的是,为什么到现在了,还会有正在复制中的居民楼。现在究竟是什么时间点,处于物质历史的什么位置。
我应该过去戳一戳复制之中的 12 号楼,敲击一下。
但不是很敢动它。算了。
过了一会,用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十分钟后,拷贝就结束了,12 号楼变成了沉重的一个,发出听不见的蜂鸣,有着渺茫的引力,不知道是由三个还是几千个它自己叠在一起。它已经是普通的居民楼了,在雨后的垡头,淡淡地矗立着。它灰扑扑的样子,就是生活本身的样子。
我错过了一个奇观,但能撞见过程已经很幸运了。不知道是不是偶然。
我从一种知觉缺失的状态里回到了现实,购物袋子勒得手指发凉,这是寻常的一天,还有很多事要忙,还要给李约买一个玻璃马。
这次之后,我意识到拷贝这种事,存在很多特例,12 号楼只是特例之一。
大地影院,大地影院很可能是没有拷贝的,只有一个大地影院在那里。这样其实也算拷贝,就是乘以一而已。垡头的大地影院屏幕很小座位很脏,但我喜欢去那里看电影。一旦你知道它只是乘以一,就会感觉坐在里面非常放松。好像如果有什么不测,乘以一的大地影院是最不容易湮灭的那个。如果不是走进大地影院,我很难意识到平时自己是一直处于焦虑中的。是那种完全不可能消除的、根本上的焦虑。
许多的风景好的景区,令人感动的山谷,都是乘以一的。
另一个特例,是一个宫,应该就是雍和宫。我从来没有去过雍和宫,长久不去,导致现在已经没法再去了。一想到要买雍和宫的门票,心里就有巨大的压力,像是社交压力。我害怕面对雍和宫。但我见过太多雍和宫的新闻图片,烧香的人拥挤不堪,在想象中,有时候觉得雍和宫是暗红的,有时候觉得雍和宫是深蓝的。但都非常寒冷。雍和宫是经历过多轮拷贝的事物,可能有一次是乘以二,又有一次是四五个,多的时候,也许一个早晨就原地拷贝了几十万次。
我还记得北京奥运会那年,加班打车路过雍和宫的时候,远远看到一个喇嘛坐在德胜门桥上,背对着我。按照常识,如果喇嘛背对着我,那么喇嘛就是没有正面的。只有一个暗红的背影,我看着这个背影,想起了克什米尔之子,还有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歼击机,银灰色的涂装,在阳光下翻转。车开近了,在经过他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他屁股底下垫得不是报纸,也不是塑料袋棉垫子什么的,而是一个概念。
这件事我记得清楚无比,但无法描述。德胜门桥上的一个喇嘛,是如何坐在一个概念上乘凉的。不知道这个喇嘛是不是雍和宫的一部分,如果他也是多次拷贝的结果,就难免会有不寻常的地方。
还有景山,景山在原地进行了漫长的、极大量的拷贝,多到无法想象,所以有人会觉得,景山在气质上有所暗示,你带着火腿肠爬上去的时候,甚至能感到景山向你举下巴,但这都是玄学。
而人这种东西,却少有喇嘛那样的特例。
我很清楚自己是经过拷贝的,以此类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类大概都是拷贝之后的产物,也是最容易出现解离的一种。人的结果都不太好,我的曾祖父,捻军的后代,就在朱庄被人在哲学上杀死。苏老师的儿子,死于渔船一软。还有大量的精神病人,徘徊在早春的
夜里。
在这个世纪,仍然有两个如芒在背的问题:本质有没有可能吞食多余的本质而合并为新的唯一本质,本质与本质完全一样又何谈复制,更不用说排异和解离。
不清楚,我很忙。而且现在的科学,还不能直接观测语义。
想去研究的话,只能凝视,比如盯着墙,水杯,电视机,芹菜,等一些冗余的东西消散。
李盆的作品有着奇妙的叙事角度,这个角度是一种在主人公内部的远观,就像你胃部的一粒电子,对整个的你的那种远观。一种微观的宏大。对这样的写作天分感到嫉妒。
——多抓鱼CEO 猫助
李盆发明了一种新的修辞,那就是按摩。锤击着读者的语感和思维方式,直到它们发热、翻身,并自愿舒展成另一个样子。
——编剧 梁边妖
李盆的关键,是他捅到了极少有人用笔尖能够抵达的物种起源。野生蒜,文字谷物,城中村个人调查,现代蕨类,老树上刷下一个新号码,咬不断的社会学,当代贴吧艺术,响铛铛是用手打了这些个,连诺贝尔奖都还没有啃到的块状不明文学物体。实属罕见,而且,在我看来——非,常,绝。
——广告人 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