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新英格兰到中国
1924年1月的一个午夜,我伫立在上海码头,寒气刺骨,漆黑一片。我不安地望着那艘向我头上压来的光线暗淡的中国船,听着船员们用陌生神秘的语言在谈话。我是一个医疗传教士,正前往福建内陆,到那新奇未知的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去。这艘将要带我开始新生活的船已经到位.可是我因寒冷而颤抖,心中又慌乱,竟然抬不起脚去登船。
正在此时,两个中国姑娘来码头送我了,她们是黄燕玉医生和她的护士朋友蔡安娜。我在费城曾经跟黄医生一起实习。她们脸上的微笑和抱着的礼物赶走了我的恐惧。她们笑着说了许多旅途要注意的事,这使我有勇气爬上船的甲板,向我的传教士生活迈开了义无反顾的一步。当船缓缓离岸时,她们的话还从黑暗中传来:“你不是一个人,上帝与你同行。”
我为我的孱弱而羞愧。她们两位并没有从小接触主,她们是在美国学医时皈依的。她们不会知道,尽管我有传承有教育,但我并不清楚上帝是什么。虽然我在传统的主内找到安慰和平安,但我的心中总是翻腾着许多问题。其实,就是这种疑问,这种对真理的追求间接地驱使我来到中国。我觉得在为主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这艘运木船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船上没人懂英语,我又一句中文都不会。第一天我全天躺在椅子上晒太阳,回想我的生活。我记得在我11岁的某一天,我擦拭家里那个带有可爱的小橱柜的写字台。当我拉开一个抽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本老旧的塔夫脱医学院的手册。我坐在地板上从头到尾把它读了一遍之后,我决定这辈子就要做医生了。
我父亲是一个勤勉的新英格兰农夫,他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多石的山坡上耕种上百顷地,供养一个七口之家。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感情内向,白天整天工作,晚上就埋头看报。我不记得我跟他有过什么对话.不过我总喜欢跟他下地或骑马上市场。我习惯于看着他的黑头发、闪亮的黑眼睛和很白的皮肤,猜测他的思想,不过我从来弄不清他在想什么。
母亲有着蓝眼睛和棕色的头发,喜欢读书,每逢星期天就带着5个孩子上教堂,可是我父亲反对去。他们因这事常常吵,我们孩子们从来搞不懂为什么父母一个认为上教堂非常重要而另一个却十分反对。我家里人不谈志愿和梦想,也不谈宗教和性。我从小就学会把自己的思想深藏起来。
高中毕业后我就为上医学院做准备。为了攒出医学预科第一年的学费,我教了3年书。德文是入医学院必需的,我就在晚上去读。我骑马跑3英里到威廉斯堡市中心,从那里换电车再跑8英里到北安普顿的人民学院(People’sInstitute)去上课。
我被医学院录取了,这一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我告诉父母,我要到波士顿去读医学院,准备听他们的反对,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搞不懂。为什么一个姑娘要去学医。但是他们表示,如果我要去,而且存了足够的钱去读,他们没什么可反对的。
这年秋天,我骄傲地穿过塔夫脱医学院的走廊,交了第一年的学费。虽然我只剩下lO美元,但我并不为此烦恼。在波士顿找工作不难,不久我就当了餐馆招待,挣的钱够我吃住。我热爱我的新生活,包括学习和工作。我喜欢志同道合的同学。生活并不轻松,但是很快活。
1920年,我在医学院的第三年,在一个星期天,我出门散步,休息脑子和眼睛,准备晚上还要用功。顺着特莱蒙大街走到哥伦布路,我注意到一座灰色的教堂,门口有一个布告,说是中国医生玛丽·史东作报告,时间正是当下。我很好奇,就走进教堂找了个座位坐下。
在随后的一小时里,我听这个娇小的勇敢女人讲述她的国家,那里成百万人没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成千的婴儿在出生时死掉,年轻的母亲因产婆无知而受到感染。听着她的讲述,我仿佛看到了中国有许多盲人终生只能乞讨和挨饿,仿佛听见许多疯人被关在黑屋里,锁在柱子上,甚至被他们的家人杀掉,因为不知道如何治疗他们。整个村庄被瘟疫毁灭,一些省份被洪水和饥荒蹂躏。史东医生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就下了一个决心,要把我的能力和知识贡献给中国的医疗事业。
我1921年从塔夫脱医学院毕业时只剩五毛钱,还不够坐火车回威廉斯堡!我从不向任何人借钱。我拎着手提箱从洛克百利(Roxbury)顺着亨廷顿路走到公共图书馆,在那里查找报纸,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在富兰克林广场妇女旅馆。
我在费城实习时,有一个漂亮的中国同学黄燕玉医生,玛丽·史东曾经是她的启蒙者。当她问起我的打算时,我给她讲了玛丽·史东和我的决心。我很惊奇玛丽·史东也影响了她,让她学医并且到美国来深造。
“中国的情况很悲惨”,她轻柔地说,“中国需要医生和护士去教育和治病。你的决心很了不起。不过,你要弄清楚你确实想去,在那里生活不容易。”
黄医生给了我传教协会在纽约市的地址,如果想被派去中国,我需要到那里去申请。我交了申请,提供了介绍人。3个星期之后,来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是该协会只接受美以美教会信徒的申请。
我在申请书上说我是公理会成员(congregationalist),尽管我从来弄不清这些教派的教义是什么。说实话,我觉得那些教义不合逻辑彼此矛盾。为什么一个处女生了一个人,这个人死后又复活这件事就构成了一个宗教的基础呢?也许他就是这么被生下来,也许他确实复活,可是这些跟宗教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宗教的基础应该是生命哲学,是一个人对人和事物的最深刻的认识。神话和神迹怎么能是基础呢?不过,我从来没对别人讲过我的这些想法,怕被别人说成异端。
面临这种荒谬的局面——我被拒绝仅仅因为我是公理会教徒而不是美以美会教徒——我决定加入美以美会,这比重新申请重找介绍人容易。这样做了以后,美以美会传教董事会就召我到纽约去面谈。
我被引到一个大房间,那里有12个黑衣女人围坐在一张长桌周围。经过短暂的审视,她们请我坐下。她们问了3个一般性问题——我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医学背景。然后问:“你是否进修过圣经?”我有些迟疑,母亲领我们5个把圣经学得很透,但我觉得这种学习可能不符合她们的要求。于是我说我没有进修过圣经课程。黑衣女人们商量起来,脸色似乎不太好。
在等待决定的时候,我的思想飘到儿时糟糕的主日学校。老师讲得很教条,我爱提问的灵魂拒绝接受。真理怎么能不合逻辑呢?那年我13岁,每逢星期天我都不出声地坐在那里忍受。有一天老师举了一个旧约的例子,然后就宣称,这个例子证明了,信上帝的军队总是赢。我心中的叛逆和不满一下子爆发了,我激奋地说:“如果双方都信上帝呢,那会怎么样?”老师严厉地瞪着我,一言不发,教室里静得可怕。我不知是怎么离开教室的,我再也不回去了,觉得被孤立起来就像个麻风病人。
黑衣女人们磋商完了,脸色严肃。我正想着一个医生会怎样因没修圣经课而被拒绝,她们就问我是否愿意修一个圣经的函授课程,我回答说愿意。我想我虽是不得不修,但是确实也有兴趣。她们又讨论了一会,然后宣布我被接受了!
我的家人对我的中国计划比较冷淡,就像当初对我学医一样。他们不在乎我的抱负,只在乎此行本身。我们新英格兰人感情不外露,除非是发火了,我们从不交换深层思想,请问这怎么能互相理解呢?
我和姐姐瑞切尔过去常拿传教士取笑,说他们拿钱比看门人和清洁工还少,却放弃在美国的好生活到海外去劝异教徒放弃他们的信仰,相信我们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确。现在我也是一名传教士了。我暗下决心,我要尽力去理解那些我教育的对象。我教他们卫生的生活,但我决不强迫他们信我们的教。事实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信什么,只知道我疑惑什么。我心里的叛逆和负面思想,没法告诉别人。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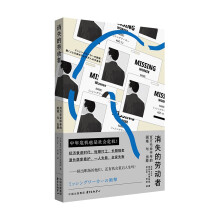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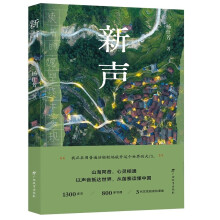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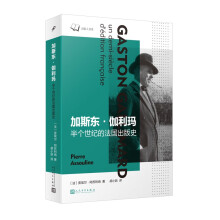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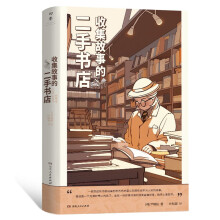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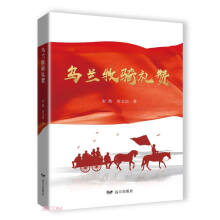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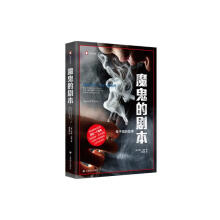

读完此书之后.我因为感动,不由自主地开始翻译。
——张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