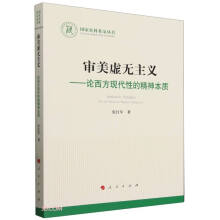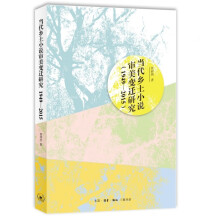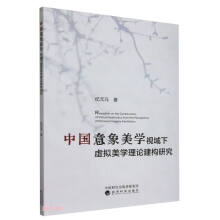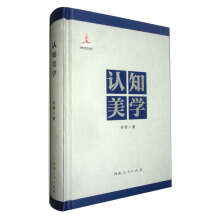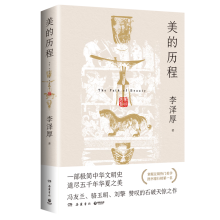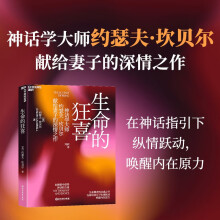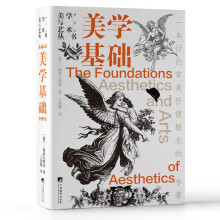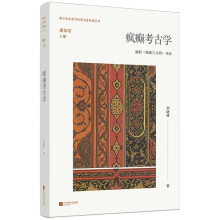讲故事不一定非用侦探小说模式,但侦探小说是最能体现故事情节集中性、整一性之小说类型。
侦探小说大概可以算是“行动力”最强的小说。
侦探小说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悬念或秘密展开。侦探小说利用悬念这一个点,延伸出一条叙事之线,叙事之线发展到某个阶段,累积的证据以及侦探的诠释,会使得“线”的性质发生改变:之前看似没有联系的各个疑点将被逻辑化地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案情有了清晰的脉络。侦探小说叙事之线的两端分别是预设的悬念与真相大白的“发现”,“发现”让之前“线”的每个环节都有意义。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言的“突转”与“发现”,侦探小说就失去了吸引力。无论复杂与否,侦探小说是用整条叙事之线去成就最后的“突转”与“发现”。“线”的一个又一个环节的累积都是为末端的“突转”与“发现”累积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惊异。或者说,侦探小说是以整条“线”成就一个最终的“发现”。这与从“线”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和端口不断延伸各类话题的现代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小说写法。
当然,侦探小说也需要很高的技巧。侦探小说的悬念设计的巧妙,不但在于悬念要有足够的分量,即案件本身要有足够的新奇性和震动性,侦探小说还要设法让悬念“悬置”足够久的时间,并在“悬置”过程中让其不断接受各种事件和误判的干扰。
干扰将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一个个看似逼近真相的答案通常是小说家所设置的推理误区:假相越具有迷惑性,情节便越有吸引力。
然而,真相大白之时,之前所有的迷惑便不再是迷惑,所有的难题便不再是难题。
这就是侦探小说的悖论:复杂性与简单性同时是侦探小说的两面。
不复杂就无法为悬念找到“悬置”的理由,不简单就无法将看似复杂的案情落实到坚实的推理思路上。
所有的细节和情节最终都服务于悬念的解答,所有的人的情感世界都被案件形成的漩涡所吸纳,所有的漫不经心的闲言碎语或看似无意义的举动最终都为唯一的真相所统率。
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不乏个性,但其个性拓展同样也受到案情侦破叙事的限制。很难想象一位侦探小说作者在描写一位侦探时会花上大量篇幅叙述他对英国山楂树的奇异体验或是来上一长篇关于“厌烦”的哲学思考。当然,文学作品确实也出现过多愁善感的侦探形象,比如罗伯·格里耶《橡皮》中的侦探瓦拉斯。然而这个瓦拉斯与其说是一位精明的警探,不如说是一位内心里不断涌现怀旧感伤思绪的诗人:“是什么厄运,使他今天不得不沿途到处都要提出解释呢?是否由于城市街道布局特殊,迫使他只好不断地问路,而得到的回答,每一次都使自己走了弯路?过去他曾有过一次在这些意想不到的分岔路口和死胡同中,游来荡去迷了路——特别是那些死胡同,更是容易叫人迷失方向——幸亏由于偶然的机会,最后找到一条能够一直走到底的路。当时只有他母亲单独为此担心。后来他们母子两人走到这运河堵塞的一端;在阳光的照射下,河畔低矮的房屋,在绿色的河水中反映出古老的建筑的正面。这一切大概是发生在夏天里,是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城市停留一下(他们是到这儿南面的海边去度假,和过去每年一样),以便去探望一位女亲戚。他好像记得这位亲戚在生气,似乎有一件继承遗产的事或类似的问题。他确实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吗?他现在甚至想不起他们最终有没有见到这位太太,他们是否一无所获就离开(在转车中间只能有几个小时的停留)。再说,这些真的都是回忆吗?关于这一天的经过,他过去经常听到说:‘你记得的,当时我们去过……’不,不是记得,他是亲眼看见那运河的一端,那些反映在宁静的河水中房屋,以及那拦住河口的低矮的小桥……还有那废弃的旧船的残骸……不过很可能这一切是在另一天,在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也可能是梦境。”④在这位不断“走神”的侦探的思绪中,城市的布局已经不是追踪罪犯的空间,而成了伤感怀旧的地点。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一位犯糊涂的侦探,说的就是破案过程的荒诞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