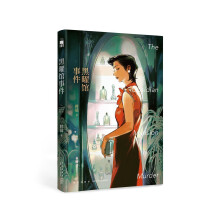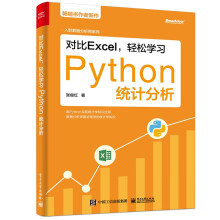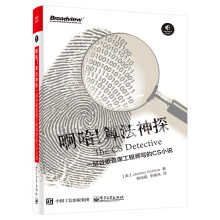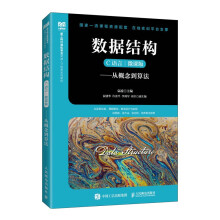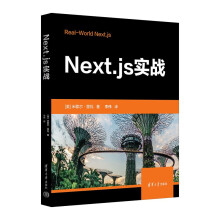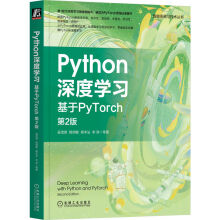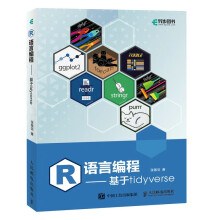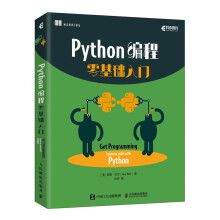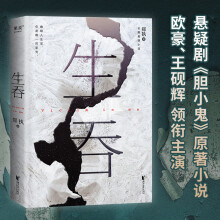第一章帮助是什么
有益帮助与无益帮助
帮助行为是复杂的,分为有益帮助和无益帮助两种,本书的目的就是阐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我担任教授和负责咨询工作期间,我经常思考一些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帮助是有益的?为什么有些课上得很成功,而有些却很失败?为什么辅导性学习和实验性学习往往比正式的课堂教学更成功?当我与企业客户一起共事的时候,为什么关注过程比关注内容更加立竿见影?如何同时做很多事而不是只做一件事?我旨在本书中为读者提供足够多的视角,能够真正地为别人提供急需的帮助,在自己需要帮助时也能得到及时的帮助。而这两种情况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例如,有个朋友某日曾就如何处理他与太太之间的一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向他提供了一个建议,结果他不仅怒气冲冲地说自己试过了,根本不管用,还因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含蓄地批评我太麻木不仁。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亲眼目睹过的很多有关求助和帮助的情形,结果无一例外地给人一种失败和难堪的感觉。
然后,我又想起一个有益帮助的例子。那次,当我在自家屋外的时候,一位女士将车停在我身边,问我:“去马萨诸塞大道怎么走?”我问她要去哪里,才知道她其实是要去波士顿市区。于是,我给她指了直通波士顿市区的路,并告诉她不需要经过马萨诸塞大道。她对我给她指明了捷径而深表感谢。
我最常见的无益帮助出现在计算机培训师和客户之间。当我拨打帮助热线的时候,计算机培训师通常会提出一些问题以确定我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但大多数情况下我甚至连问题都听不懂。而当计算机培训师告诉我解决问题需要的步骤时,我不知道如何打断并告诉他:“等等,我不知道第一步如何操作。”另一方面,我的另一个计算机培训师则直接问我学习使用计算机的目的是什么,当得知我学习计算机无非是用来写作之后,他便向我展示了用于写作的所有程序和工具。这种感觉真不错。但是,当我的太太向我求助计算机使用方法时,我也毫不例外地陷入同样的陷阱,我对她解释计算机操作步骤,结果她根本跟不上我的讲解速度,最后,我们两个都觉得非常灰心。
朋友、编辑、顾问、老师和教练经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跟问题毫不相关的建议和提议。即使我尽量以礼貌的方式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但有时候对方会用一种恼怒的语气提醒我他们只是想帮我,言下之意很明白:我不接受他们的帮助是不对的。
我记得我的孩子曾因数学作业向我求助,我停下手中的工作,给她解答了那道难题,结果她连感谢的话都没说,还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我做错了什么?还有一次,家里的另外一个孩子也在家庭作业方面寻求我的帮助,于是我对她说:“我们先谈一谈吧……”然后,我发现她原来是想跟我讨论一下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与家庭作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友好的谈话,双方都感觉很好。
不管是医生、医疗专家,还是社会工作者、培训师,所有人都有过好心好意提供帮忙却不被领情的经历。我曾在各种机构里担任过咨询师和经理人职业培训师,经常为经理人和企业提供问题解决方案,但后来我发现:要么是我的建议根本无法实施,要么是客户根本无法或不愿实施我的建议。我记得在咨询的过程中,当我指出一些机构存在的机能失调等问题时,那些咨询者总是对我的帮助深表感谢,但后来我常发现这些方面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改善。
当然,帮助关系并非仅限于个人之间,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能否实现取决于团队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履行职责、完成团队任务。通常情况下,一个有效率的团队并非由真正懂得如何通过互助完成某项任务的成员组成,事实上,这正是真正的团队精神之所在——成功而互惠的帮助关系。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团队成员只有在需要帮助时才会提到“帮助”这个词,例如,一个成员对另一个成员抱怨:“你根本没帮上什么忙”或“你为什么不多帮我一点儿”!
团队内的互助在团体运动中体现得最明显,在团体运动项目中,一个成员的得分完全取决于其他成员传球和拦球的技能。许多橄榄球队的跑卫在赢得一场比赛后都会请线卫吃饭,以感谢他们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四分卫被擒抱或跑卫在线后被擒抱,那么此时任何人都将是爱莫能助。
显然,求助行为与施助行为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事实上,这种看似普通但又必需的人类行为常常是困难重重,很难让双方感到满意。本书的理论前提是:帮助行为是一种重要而复杂的人类活动。我要分析以下方面:求助行为与施助行为的意义;帮助过程中有哪些心理、社会和文化困境;如何避免这样的心理、社会和文化困境。上文的例子说明帮助行为不仅限于医生、律师、牧师和社会工作者所提供的职业性帮助,还包括很多其他类型的帮助。那么帮助行为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如何保证帮助行为行之有效呢?
帮助行为的多重含义
帮助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既有身穿盔甲的骑士拯救少女于恶龙之口的侠义之举,也有咨询师帮助企业变更企业文化以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提高绩效的善意帮助。从受助者的角度来看,帮助行为不仅是我们请求得到的东西,也是一种自发而慷慨的行为,即使我们不开口求助,施助者也能意识到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想一想日常生活中的帮助行为吧(见表1.1 )。帮助行为在所有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都随处可见,表1.1 中描述的很多种角色就是我们根据不同场合的要求而扮演的。进一步说,帮助行为对各种组织和工作是一种本质需要,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之所以要组成一个团体,就是因为我们个体无法完成整个工作。付费施助者不只是仆人和看守入,也包括所有团体聘请的那些负责某项工作的雇员,因为任何团体的组织者本人都无法独立完成该团体内的所有工作。因此,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是我们对别人施助的常规方式。我们再想一想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吧,当下属没有尽力完成任务时,或者老板没有为员工留下完成工作的时问和其他条件时,上下级关系自然会比较紧张。雇员与老板会根据他们互相之间的期待而达成一种心理契约。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概念的广泛性,请留意一下我们用多少种不同的名称称呼“帮助”一词(见表l.2 )。这些帮助过程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点?要提高帮助的质量,施助者与受助者是否需要更好地理解帮助的文化含义?现有的帮助行为多种多样(物质帮助、情感支持、信息、诊断、建议与推荐等等),我们需要对这些帮助行为加以区分吗?他们的相似点与差异体现在哪里?
正式帮助与非正式帮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帮助行为是一方要求另一方解决问题、完成任务或缓解压力的一种行为。受助者或许能够独立完成某件事或许不能,但帮助行为的发生意味着这项任务在施助者的帮助下应该会更加容易或者完全得以解决(比如拯救一名溺水者)。因此,帮助行为是一个需要合作、协作及各种利他行为的过程,我把此类帮助行为称作“非正式”帮助。在所有文化体系中,这种帮助行为是约定俗成的,被看做“文明社会的基石”。
帮助行为的下一个层次可以被看做“半正式”帮助,也就是我们寻找各种技术人员帮助我们修理房屋、汽车、计算机和视听设备等行为。在这种层面上,我们需要的帮助是让这些物体正常运转,我们个人在这种帮助行为中参与的成分很少,只用为这种服务和信息付款即可。在此类情况下,不管是受助者还是施助者,我们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均来自于我们对这种帮助行为期待过高,我们往往希望看到被修理后的物体能够更容易操作,却不愿意接受计算机等设备所要求的新语言和新程序。
当我们遇到某些个人、健康和情感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正式”帮助,需要那种经过授权的医疗、法律和精神帮助,我们会寻求医生、律师、牧师、咨询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精神病专家的帮助。在管理和组织工作中,当我们遇到管理和组织执行力等方面的问题时,我们会拜访各种咨询帅。在这些情况下,帮助行为来自于专业人士,通常要通过合同、时间表、现金等更加正式的程序获取服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