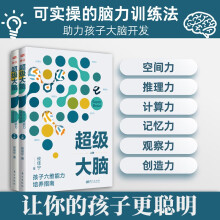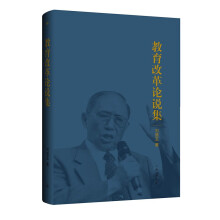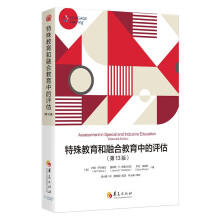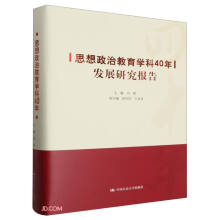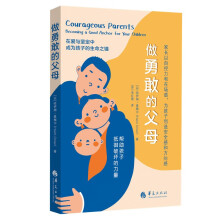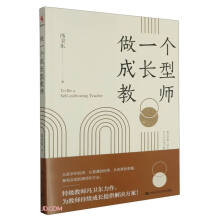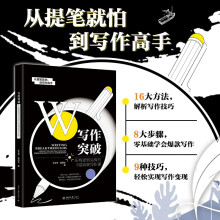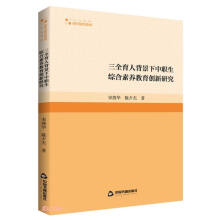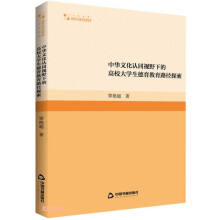群体性与个体性共存。布迪厄认为:“惯习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致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布迪厄等,1998)这一描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惯习具有群体性,总是为同一阶级或群体的所有成员所共有,是体现在同一场域内不同个体身上的集体倾向系统。布迪厄曾明确指出:“同一阶级的所有各个成员,都具有比属于其他阶级的任何成员更多的机会,去设身于其所属阶级其他一切成员最经常面临着的那个环境中。”(高宣扬,2004)”。也就是说,同一阶级或群体的社会成员所面对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条件相似,面临基本相同的生活情境,更有可能形成相似的性情倾向系统,具有相似的惯习。另一方面,惯习具有个体性,经过个体的内化,惯习在同一场域内不同个体身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同一场域内,不同实践主体所处的位置不同,所拥有的力量不同,实践主体进入该场域的奋斗历程或人生经历也存在差异,所以场域内每个实践主体的惯习也不尽相同,如布迪厄所言,每个个体的秉性系统乃是他人秉性系统的一个变种(高宣扬,2004)。但归根结底,差异是相对的,相似是绝对的,“个人风格,不过是相对于时代的或阶级的风格的偏离”。在某一场域内,实践主体总会拥有一些相同的惯习,正是它们维持了场域的运行和独立存在,如布迪厄所言,“人们之所以对他们遭遇的现时所限定的某些未来的后果‘萦绕于心’,只是其惯习激发他们、推动他们去体会这些后果,追求这些后果所致”(布迪厄等,1998)。场域虽然形塑了惯习,但“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布迪厄等,1998)。
被建构性与建卡勾.眭共存。社会结构影响着惯习,同时惯习又形塑着结构,惯习具有主动的建构性和被动的被建构性。惯习作为一套性情倾向系统,通过个人的社会化而实现社会结构的内化,这种内在化的社会结构,在特定场域内的主体身上表现为一致的系统反应,这种反应是主体应对场域要求而做出的可预见和有规律性的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惯习是被建构的。同时,惯习又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布迪厄等,1998)。惯习作为一种“产生与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理”,通过与现实情境的遭遇,形塑社会结构,这又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对惯习作为“结构形塑机制”,布迪厄还曾有这样的经典描述:惯习“是持久的和可转换的秉性系统,是被结构化的结构,亦是起着结构化功能的结构的‘前性情”’(高宣扬,2004)。布迪厄不厌其烦地使用“结构”一词,拗口地创造出“被结构化的结构”、“起着结构化功能的结构”、“结构的建构”、“建构的结构”等短语,其用意仍是强调惯习调和主观与客观、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独特价值。这在他的另一段论述中也有体现:“惯习,作为一种处于形塑过程中的结构,同时,作为一种已经被形塑了的结构,将实践的感知图式融合进了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之中。这些图式,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布迪厄等,1998)。
有意识与无意识共存。惯习是个难以把捉的事物,它们“在意识和语言的水平之下发挥功能,同时也超越了意识控制所能及的范围”。换言之,惯习作用的发挥似乎是人们可以感觉到的,是可以意识到的,但惯习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又是人们无法计划、掌握和控制的,是无意识的。布迪厄曾说,惯习能“客观地适应于它们的目的,而又无须设定这些目的的有意识的目标,也无须设定对达到此类目的所必要采取的步骤的专门控制;同样地,它们也能客观地加以调整和正常化,却又无须成为顺从于规则的产物。总之,作为这样的一些事物,它们总是被集体地交响乐式地演奏出来,但又无须成为一个交响乐队总指挥的组织行为的产物”(高宣扬,2004)。这段论述将惯习有意识与无意识共存的特点相对具体地展现出来。惯习是一种非形式化的实践性知识,虽然在实践中呈现,却不能有意地计划、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惯习是一种已经内化到个体身上的体知。惯习在实践过程中生成,人们受惯习指导进行实践时却是前意识的、无知无觉的。也就是说,惯习作为一种实践的逻辑,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但又无法精确捕捉,因为“实践逻辑的逻辑性只可以提炼到特定的程度,一旦超出这种程度,其逻辑便将失去实践意义”(布迪厄等,1998)。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