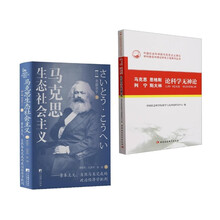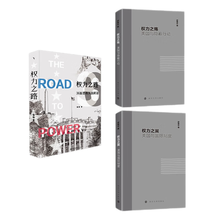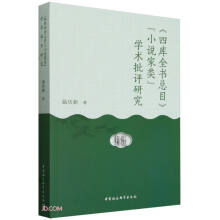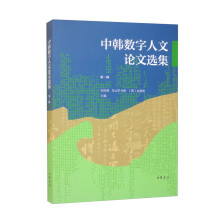五、网络社区互动中的主体
网络社区中的诸结构构成了行为主体。在话题提出到统一行动过程中,社区网络上任何结构的作为,都可能通过“蝴蝶效应”影响整个体系。
1.发起人
发起人的意见和信息构成了某一议题的直接来源,其在网络社区互动中的作用自然不容小觑。发起人往往包括四类:猎奇者、幸运者(指那些偶得他人遗失的相机或手机,然后将其中的信息公布的人)、利害关系人和活动组织者。
2.重要资源占有者
这类人对事件最终发展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主体包括:政府相关部门、网络社区意见领袖和拥有特定能力者。政府相关部门拥有的资源是权威和信息,意见领袖和特定能力者则拥有利用专业知识和能力影响舆论的能力。
3.一般网民
在网络社区中,广大普通网民常常成为正义的代言人。如邓玉娇事件中,网民的呼声使得案件的判决出现了极大转向。有趣的是,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个体行动的逻辑,很多人都与网络事件没有现实利益关系,但他们却力主社会正义,自愿为受害者提供舆论支持。
同时,网民的网上互动行为与其现实生活并非截然分离,网民对现实生活中腐败等问题的理解通常会投射到其网络言行上。六、网络社区互动的基本机制:一种比较视野
1.网络社区互动的基本特点
结合现实生活和以上案例分析,不难发现,人们在网络社区中的互动方式与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差异。
1)匿名性
网络舆论的真实性和背后的言说者往往难以判断。鉴于目前未全面实行实名制,网民在网络社区中的身份代码只是一个富有个性的网名,甚至只是一个IP地址。这种匿名性常常是虚假信息的根源。
2)传染性
便捷的现代通信技术和开放的沟通平台使得信息可以在数秒之内传播给网络社区内所有人。伴随着信息传染而来的是情绪传染。正如上文所述,各网络社区相对是同质的,网民在这一体系中与其他结构和体系相互影响,这种“较有人情味的方面”本身为各种有意鼓动、情绪化宣传提供了有利土壤(赵定东等,2010)。同时,各网络社区又可以通过各个网名联系起来,从而加速传染。而按照勒庞的观点,当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时,即使一个独立时能够保持理性头脑的人,也会表现出去个性化的特征,呈现出从众、过激倾向。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其背后是否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因素。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许多媒体在社会报道方面不尽全面,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体验却是真切的,当某一能够引起共鸣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时,广大网民常常能够很快动员起来。
3)个性化与极端化
乍看起来,个性化与去个性化是矛盾的,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体两面,二者相当程度上都源自网络社区的扁平化结构。由此,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都能就某一主题发表评论,但很少有人能对他人施加绝对的影响力。所以,一个想要引起关注的网民就得充分发掘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出奇以吸引眼球,这就解释了各种极端言行、造句接龙活动、歌曲改编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同时,整个体系中的舆论对个体结构的极端言行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4)去利益化与道德化
网络社区互动中最为显著的是,某一信息或者事件的关注者往往与其关注对象并没有明确的利益关系,其背后的根源值得研究者深思。另外,网络社区中的个体通常会都站在一个道德至高点上对各种事物予以评判,并促使一些问题的解决多少带有道义色彩。已有学者觉察到这种趋势,并对这种网民力量表示担忧,甚至有人警示,在个别案例中,网民的过分要求和过激反应已经干扰了司法程序。实际上,这种道德化背后,是广大网民对现实生活的普遍不满,经受了长期压抑后,他们需要以一种理想主义方式进行发泄。换句话说,这种道德化源自环境对于体系和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造成的网络舆论的道德化、理想化、极端化并不是好的信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