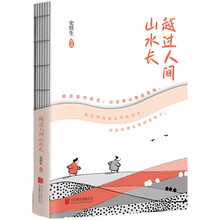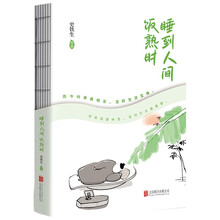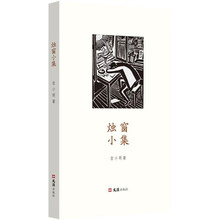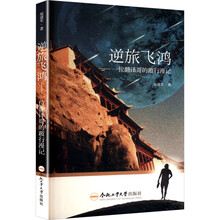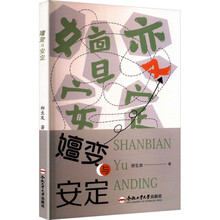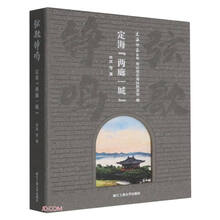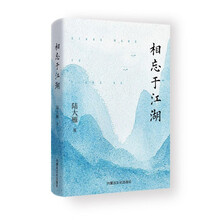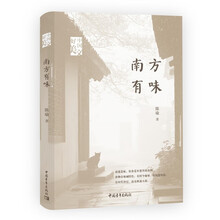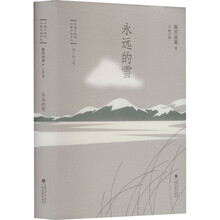1944年的暮秋,我从南温泉移居到北温泉去,秋天是雾季的序幕,整个的赤色盆地沉醉在乳浆般的迷蒙情调里,从北碚到温泉的小船是像蚁般地密布在嘉陵江上的,我们的船儿扬起小小的白帆,让润湿的秋风吹送着,沿着松软的沙岸缓缓地上溯,起伏的峰峦欣迎我以葱郁的绿色,而照映着起伏的峰峦的江水正蓝得发亮,蓝得使我在心坎里深深地觉得它的可爱;船儿进了大渡口,低沉的天空陡然显得高了许多,最先吸引我的视线的是温泉寺的琉璃瓦棱,和高大的红墙、虬曲的古柏构成一幅古典的风景画。
我需要在这静悄悄的山国静悄悄地休养一些时候,我在半山的一座小小的别墅里住了下来,房子四围有疏疏落落的竹篱环绕着,紫藤花虽然已经凋谢了,枯萎的藤依然紧紧地拥抱着篱笆,屋檐上偶然有三两只麻雀交换些短短的对话,倒把这寂寞的气氛衬托得更加寂寞起来。
窗子里望出去是一片衰败的竹林,终年很少有人的脚迹,显得荒凉而幽暗,地面上平铺着些薄薄的苔藓,让蝾螈和甲虫在上面舒适地漫步,当它们踏到落叶的角落,便有一阵轻微的声音发出,竹林的尽处横睡着一条废弃的公路,如今只有赶市集的人走过,只有放牧的村童驱着牛群和羊群走过;再远是绵亘无尽的茶褐色的山岗,一直伸展到远方。
走出篱门,是一块浅草茸茸的平坝,后来我常常在坝上打羽毛球,或是作为日光浴的浴场。
生活是闲适的,每天早晨在左近散步的时候,偶尔也采撷一些花束插在花瓶里面,用水养起来。整个的上午,我总是躺在藤椅上的,房子里的光线比较暗,因此躺椅就放在走廊里.为了要使身体宽舒,倒是穿睡衣的时候多,雾太浓重了,或是起了风,怕受凉,情愿盖上一床毛巾被;藤椅旁是一张放茶杯和书籍的矮几,书籍里面少不了峨默的《鲁拜集》,虽然这是我早已读得能背诵的了,我对于龙井和《鲁拜集》的爱好,几乎陷入一种精神上的病态。
躺着仰望天空,使我有着置身海上的感觉。那灰沉沉的气流,不正像英伦海峡终年被白雾笼罩着的海水么?
下雨的日子,报差和邮差都不上山来,这里仿佛和整个世界隔绝了,只有淙淙的檐漏,像一个没有人欣赏的乐师在弹奏单调的竖琴,接连下一两个星期的雨是不稀奇的,我还没有完成中国书学研究会请我写的那本丛书,我计划利用雨天来读入川以后所收藏的碑帖,《兰亭序》的惆怅的情绪使我不能安宁,只有站起来吸一两筒板烟,妄想把感染来的一份惆怅,也随着烟圈渐渐地淡化。
我久已忘记了用钟的习惯,连案头日历也懒得翻了,让它被尘封着,被瓶花的残骸覆盖着,时节依然在无声无息地转换,等到我有一次从峡谷里走过,看见腊梅开了几株瘦小的花朵,才意识到原来已是岁暮了。
冬天的北泉公园是没有喧嚣的,爱莲池里飘浮着一两片枯残的荷叶,随着寒冷的波光轻轻地颤动,如今那些都市里来的游客早回到都市里去了,就是修理花卉的工匠也蛰居在家里休息了,只有我,提着一根倒钩藤的手杖,在这山风呼啸着的岁暮,在这方石板的道路上踽踽独行。
我的手杖很久很久就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在这崎岖的山中,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它的,我没有坐一次山轿的享受,我不愿意让那些比我更清瘦更憔悴的轿夫,抬着我爬一个高峻的斜坡,重压下的喘息,痛苦中的表情,魔术似地使我难以言喻地酸楚。
从温泉寺到缙云寺的中途,群山环抱着一个小小的湖泊,我曾在微雪的清晨去作初次巡礼,静止的湖水绿得那么深沉,湖畔的高大的杉树显得那么洁净,长堤上排列着一抹齐的栏杆,仿佛这长堤的彼岸就是我们所祈求的天国,微雪仍旧怕人察觉似地落下来飘下来,而缙云寺的钟声也随着雪片疏疏地飘落,在这一瞬间,我卑微的生命受到了一种感召,我愚昧的心灵受到了一种启示,我愿化身为湖水的一点一滴,我愿化身为杉树的一枝一叶,我愿在钟声里度过未来的岁月。
漫长的冬夜,炉火是我最亲切的友人。炉火的照耀,替我刻划着过多的风霜的面孔敷上一层绯红的色泽,一块杠炭的爆烈,一颗火星的飞射,就是整个冬夜值得记叙的事情,我从没有辜负过炉火的温暖的赐予,坐在炉边,要等到每一块杠炭都经过完全的燃烧,都变了热力发散已尽的死灰,我才无可奈何地去睡眠。
盖了厚被往往有梦,这在我是无法逃避的苦役,无论在梦境是欢愉是悲哀,醒来免不了空虚之感,那些人物、那些形象都很快地消失了,只有一片无际的黑暗,和黑暗中若有若无的阴影,梦是空虚的,无法把握住的,人之一生,也不过是一个冗长的梦罢!也不过些琐碎的梦底连续罢!
春天逡巡在山中,我已经稔熟每一条蹊径每一个荒僻的所在了,我发现山背后乱石堆里密布着坟墓,野蔷薇开得正茂盛,香得使我简直透不转气来,这是造物怜悯那些长眠在山野里的精灵,而特意布置得如此朴素如此美丽么?翩翩而舞的小黄蝴蝶,是死者所蜕化的么?墓地没有一块碑碣一挂纸钱,也许葬在这里的是些飘泊异乡的旅人,其实碑碣和纸钱也是徒然的,不过是后死者在觅取一点极有限的自我慰藉罢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