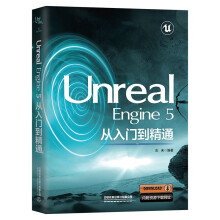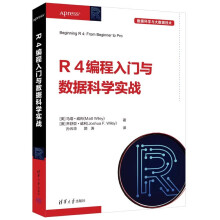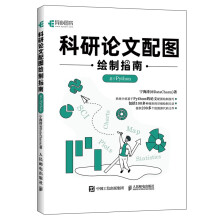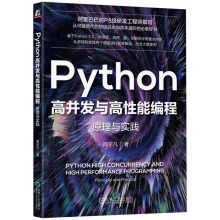第一章家庭和教育
鲁迅1936年逝世以后,被全国一致地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任何一位过去的或现在的中国作家,都不曾像这样在整个民族中被神化过。关于他的生平有过那么多的记载,对他的研究是那么细致入微,看来,再写一次传记是无必要的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偶像化,使鲁迅生平的某些方面被夸大得失去了分寸。
由于种种考虑,在本书中,我想重新从鲁迅的早期生活开始,研究使他最终成为一位新文学作家的心智历程。和那种神化的观点相反,鲁迅决不是一位从早年起就毫不动摇地走向既定目标的天生的革命导师,相反,他终于完成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是经过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而得来的。他的心智成长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鲁迅所选择的生命目的,完全不合乎那个时代知识者中的著名人物如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的功利性质。他那著名的放弃医学从事文学的决定,在作家社会地位尚难确定的当时的中国,可说是无前例的。鲁迅将自己完全投入文学事业的那种严肃性,对于他自己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个人事业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绅宦家庭,虽然已经没落,仍是一个有着显赫声望的大族。如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所细致描述的:整个周家大族分为三房,各自聚居在围着高墙的大院中,本身就是个真正的世界:房屋,花园,池塘,拱门,碎石栏杆,油漆大门,石桥,长满苔藓的小径,庭院。总之,是中国传统的缩影,虽已没落仍令人肃然起敬,正如“台门”这个词就已意味着世家大族。鲁迅生于其中的“新台门”是以其先人有学问而著称的,台门中又分为许多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鲁迅当时已经败落的家庭却是属于“兴”房的。
虽然鲁迅生于典型的传统绅宦家庭,他的祖父和父母比较自由的态度却使他所受的教育不像一般情况下那样僵化。六岁时,他首先从一位叔祖学《鉴略》,因为他的祖父认为学点历史知识对青年人是有益的。老人也鼓励孙子阅读通俗小说,特别是他自己喜爱的《西游记》,认为也有教育价值。鲁迅十一岁开始上家学,他并不喜欢正规地应读的四书五经,却对那些杂书,特别是关于幻境、鬼怪和神话的书感兴趣。他还爱好绘画(而不是练字),摹绘从亲戚和女仆那里得来的书上的图画。这些书有的是通俗小说和传奇,有的是关于动植物的画书。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不鼓励孩子们涉猎通俗小说、神话、寓言、奇幻等方面的作品的,孩子们如有兴趣只能偷看。鲁迅被允许,而且实际上坚持在这个小小的非正统的领域中探索,对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似乎铺平了他以后长期的对于“杂学”以及爱好并提倡“小传统”通俗潮流的兴趣。
至少鲁迅自己也是这样看他这些早年的追求的。在《朝花夕拾》里,最不吝笔墨的是关于民间传统形象的描绘,如迷人的“无常”、“女吊”等。这还有他自绘的图像可作证明。这个集子里有一篇长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抒情地让人看到了他儿时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百草园为象征的趣味盎然引人入胜的“小传统”世界,另一个是以他老师的书屋为象征的枯燥无味的“大传统”世界。他将老师指定应读的可厌的书和阿长给他的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的有趣的《山海经》相对比,戏剧性地说明了他对“小传统”的偏爱。这本书将幼年鲁迅引向了更多的鬼怪奇幻书籍,如《酉阳杂俎》和《玉历钞传》。这种奇幻世界对他后来的小说写作和研究都不无影响。
正如夏济安所指出的,鲁迅对他幼年时世界的描写标志着一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黑暗的闸门》,第146—162页)。百草园实际上只是屋后一个荒败的菜园,但却有着关于赤练蛇和美女蛇的迷人传说。女仆阿长和鲁迅的祖母还向他讲过“长毛”的可怕故事,后来他用这材料写了《怀旧》。他还参加过村里演社戏的活动,在目连戏里扮演“鬼兵”角色,和十来个孩子一起,按照戏里的要求,画上脸,骑上马,拿着钢叉,随着“鬼王”疾驰到城外的无主孤坟之处,用钢叉连连刺坟,邀请“怨鬼”们来看戏。幼年鲁迅对这种幻想的仪式是非常神往的。但是当他稍稍长大,开始分担家庭困难时,这种“黑暗世界”的魅力就不仅是使他愉悦,而且也困扰着他了。
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