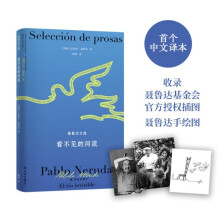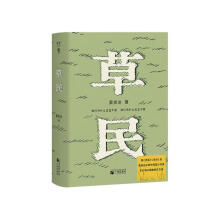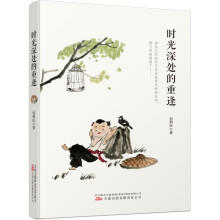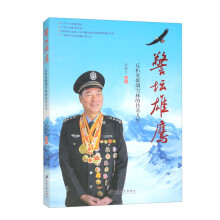空山流水<br> 某年秋,十月末。我坐在盐原帚川的支流鹿股川畔的石头上。昨夜,秋风劲吹,红叶大抵散落,河床一片艳红。左右两侧皆是高耸的山峰。夹着一带细长的青空,仿佛天上也有一条河流过似的。时值秋末,河水瘦缩。近乎干涸的细流,打乱石中间穿行。河床蜿蜒于高山深谷之间,曲折而下。远处可以看到流水的尽头。恰巧有一座高山当河而立,堵塞了河水的通路。远远望去,仿佛河水已被山峰吸入体内,又好像这山极力抱住水流,规劝道:“就停在这儿吧,流进村庄有什么好?停下吧,停下吧。”<br> 然而,河水依然流过河底的碎石,钻进红叶厚积的栅栏,高唱着歌儿向前奔去。坐在石头上,用心倾听,有一种声音!松风。这无人弹奏的鸣琴般的声音,拿什么比喻它好呢?身子坐在石头上,心儿却追思着流水的行止。远了,远了,远了——啊,依然隐约可闻。<br> 至今,夜半梦醒,潜心聆听,似乎从远处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br> 大海日出<br> 撼枕的涛声将我从梦中惊醒,随起身打开房门。此时正是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清晨,我正在铫子的水明楼之上,楼下就是太平洋。<br> 凌晨四时过后,海上仍然一片昏黑。只有澎湃的涛声。遥望东方,沿水平线露出一带鱼肚白。再上面是湛蓝的天空,挂着一弯金弓般的月亮,光洁清雅,仿佛在镇守东瀛。<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