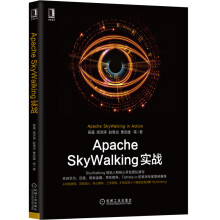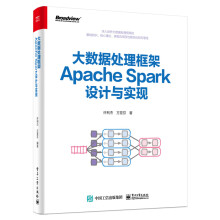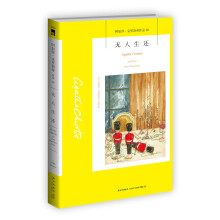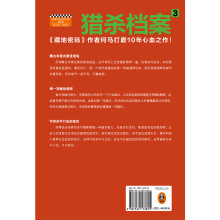新生代导演的底层空间背后,有一种对欲望叙事的质疑。在影像世界中,欲望叙事表现在主体对客体对象的生死搏斗乃至征服,对物质、权力与性的获得。近几年,好莱坞乃至全球影界的奇观电影并没有改变征服的主题,无论是冰海沉船、星球大战、魔法世界还是异域风情,一切都离不开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黑格尔认为主体“通过扬弃那独立自存的对象而存在,换言之,它就是欲望。欲望的满足诚然是自我意识返回到自己本身,或者是自我意识确信他自己变成了客观真理”①。从整体看,欲望叙事是现代化百年叙事中一个前进的动力,福柯从中解读出现代文明无所不在的权力压抑机制,一种处处以自我为主人、他者为奴隶的叙事机制。性别也好,种族也好,阶层也好,都能在主体与他者的二元游戏中找到相同的游戏规则。欲望叙事的模式不被驱除,那么“底层”进入影像依然遵循着“主/奴结构”的模式,“底层发声”的故事不过是西西弗斯神话。《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一当年的金球奖与奥斯卡奖项中的“大赢家”就是个最佳的例子,这部英国导演拍摄的“好莱坞电影”所要说的不过是一个印度版的“美国梦”而已,残酷的底层境遇不过是为了最后的欲望成真。导演苦心孤诣地嵌入一个“百万富翁”的竞猜游戏,只不过方便主人公最终获得金钱与美女。在欲望叙事的主导下,电影虽把镜头对准印度孟买的贫民窟,但这个底层空间依然是他者化的底层想象。新生代导演的底层空间中,无论县城、都市甚至全球化的漂流空间,欲望像随处飘散的蒲公英一样充盈在其中,有的是“城里人”的梦想,有的是“同步世界”的渴望,有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任逍遥”,但是在最后,这些欲望之于底层无异于潘多拉的盒子,没有美梦成真,反而引诱着底层走向拘禁、毁灭或死亡,这已全然是一种反“欲望叙事”的模式。与新生代底层空间的日常性相适应的叙事往往没有由弱至强的戏剧高潮,同时对好莱坞的镜框叙事也一并拒绝,其背后是建构主体力图全面把握世界的渴望。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