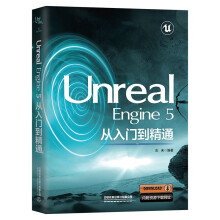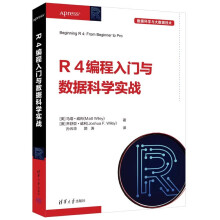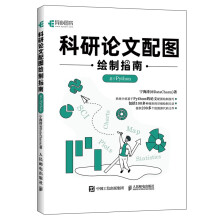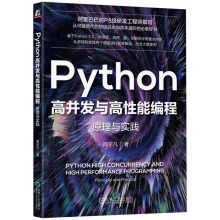自从读古人作品的,存了一个“古人作诗,托男女以寓君臣”的成见,不知埋没了多少抒情诗。诚然,古人作品中,也确有“托男女以寓君臣”的,如《离骚》之类;但却不可以执着少数的例,概尽一切。原来中国人向来主张男女有别,礼教的防闲,看得很严,总觉得男女言情,仿佛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所以不但把别人抒情的作品,看成“托男女以寓君臣”;就是自己确为抒情而作的诗,也往往甘心让人家指为“托男女以寓君臣”,作避却离经叛道的唾骂的保护色。虽然有人说陶潜“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却依旧有人把“托男女以寓君臣”的话,来给他辨护。如果清代朱彝尊没有“宁不食两庑豚,不删《风怀》二百韵”的自白,也难保人家不说他底《风怀》诗是“托男女以寓君臣”哩。
《古诗十九首》,咱们不必说它是什么“源出《国风》”;但它总是《国风》以后含有抒情诗而还被保存着的第一群,而且和《国风》同样,都是无名诗人——虽然徐陵《玉台新咏》指其中九首为枚乘杂诗;但是和徐陵同时的《昭明文选》,却只认为无名氏底古诗,而徐氏以外的选本,也都称为《古诗十九首》;现在不取徐说,我们只认识其中不是一人的作品就够了--底作品。然而历来说诗的,也爱指它为“托男女以寓君臣”;于文学上颇具特殊眼光的金人瑞,也逃不出这个窠臼,真是可叹!
这个“托男女以寓君臣”的成见,实在是中国旧文学中抒情诗的坟墓。如果要整理中国旧文学,使旧体抒情诗底“木乃伊”,有重见天日的希望,非掘去这个成见的古墓不可!含有抒情诗的《国风》和《古诗十九首》之类,咱们不可不把它们从古墓中掘出来,重新唤醒它们抒情的灵魂!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