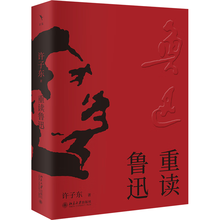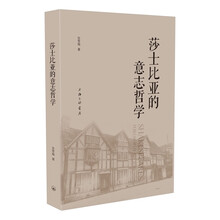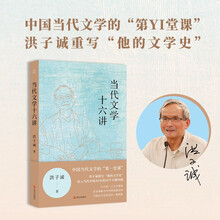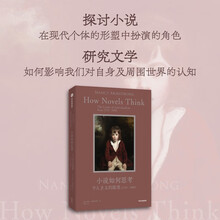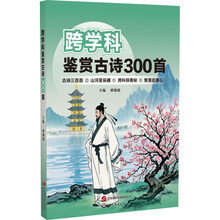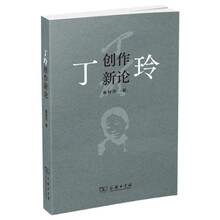新时期的文学,一开始就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就是它的情感指向都是从重新认识人开始的。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审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无一不是强烈地表现出对人的生存关怀这一点,像刘心武的《班主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故事的生活面,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历次政治斗争给人的生存带来沉浮起伏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在反思“政治”对“人性”的粗暴干涉中,表现出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关怀。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直接推动下,从1979年开始,我国学术界对人、人民性、人道主义以及人的异化等与人相关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大讨论。在这场长达数年但实际上并未结束的关于“人”的讨论中,人们终于通过学术争论,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并对人性与人的阶级性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广泛和较为深入的探讨。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观看这场争论,虽然在这场学术争论的后期,由于某些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导致这场学术争论最终无法在学术界对“人”的探讨达成共识。但它终于突破了我国在“人”的研究上的一些局限,打破了长期以来“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这种将阶级观念强加给学术研究的思想束缚,并为今后关于“人”的研究冲破种种意识形态的枷锁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一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对人以及人的生存与价值观念,又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偏差和影响。这种偏差具体表现在文学活动中,呈现出重视人的实用价值,强调人作为一种社会商品的文化符号意义。于是,人的生活意义就被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为对物质的占有,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由于人的存在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对生活被动地接受,人在被动接受时缺少一定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就会自动放弃思想的独立品格,使人沦落成为物质的工具或奴隶。像中国当代作家朱元的《我爱美元》、《生活无罪》等作品,尽管作者极力宣称这是20世纪末“现代人结束精神流浪的悲壮努力”,但其通篇表现出来的金钱至上、享受堕落的思想,即使再多包装上几层时髦的“世纪末情绪”的华丽外衣,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也只能是早在19世纪末就被批判现实主义评论家批臭了的陈腐不堪的东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