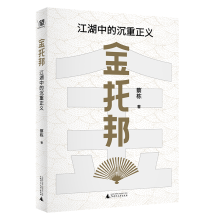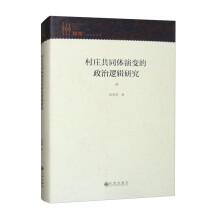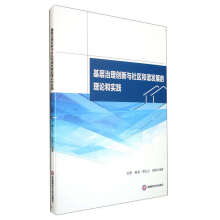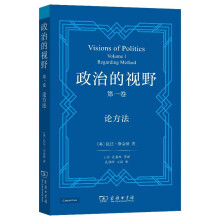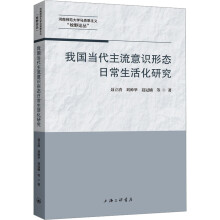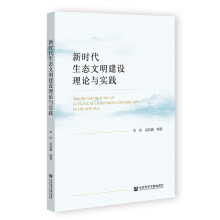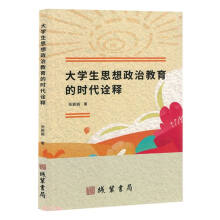当我们费了好大的工夫才留意到个体概念的历史化时,它就是一个令人陌生的观点,尽管它所处的领域非常广。在整个社会中,人难道就不关心自己和他所拥有之物吗?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1960[1893])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的疑问,“个体主义并不始于任何地方”,他如此写道:它存在于任何时期。这只是意味着,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制度(取其广义)视为一种天平:它们对于个体福利的贡献。而在文化主义那里,这个在涂尔干和韦伯关于道德演进理论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阿基米德原理,却被视为了虚幻。
我们知道如此的历史化在文化主义者那里是有用的:它可以使将各种社会进行比较的企图失去信誉。
举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的例子。如果个体的观点被用作比较一个社会和另外一个社会的参照对象,那么雅典就立即显得比斯巴达更可取。但是,如果个体观点所具有的重要性只是雅典文明在文化上的特殊性,那么要作出雅典具有优越性这一判断就变得毫无可能。至于那个对雅典较之斯巴达具有更多亲切感的人--一个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或者一个现代人,他只是一个幻象的受害者,而这个幻象来源于一个本属于自由主义社会之物,文化主义者如是反对到。
有时候,这些观点采用了一种双曲线式的表达方式。例如,美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施维德(2000)解释道,正是在偏见的作用下西方文化煽动着西方人斥责割礼,而在土著人那里,则将其视为一个美好的东西。
他用一位女人类学家的故事来支撑此论述,她成长于美国,并在此受教育,之后便决定前往她家族的发源地塞拉利昂生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