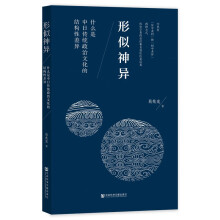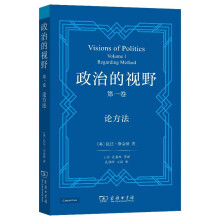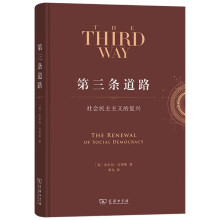任何这种语言的形成都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它肯定表现出历史的维度;它肯定拥有并限定着一个由那些社会安排、历史事件、公认的价值和它能够言说的思维方式所组成的过去;它言说着一种不能与过去的性质完全分离的政治。因此,历史学家无法轻易满足往往是由他本人提出的要求:他要把政治言说行动描述为它是由(用受到奥克肖特批评的说法)“当下的实践行动”的“初始”(primordial)要求决定的;因为语言是用包含着各种对过去的暗示的言说去描述当下的,很难把当下孤立起来,很难以纯粹当下的实践加以表述。政治言说当然是实践性的,包含着各种当下的必然因素,但是它同样在始终做着努力,要发现当下实践中的必然因素是什么,最强大的头脑在运用这种政治语言时,会探索语言惯用法和以新的方式运用语言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历史学家与这种紧张状态有着他自己的关系。他知道他所研究的语言通常包含什么规范,但他也可以拥有独立的知识,知道这些规范以及以它们作为前提的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语言尚没有办法认识这种变化的方式和原因。因此,他会寻找由于新经验的缘故,词语正在以新的方式被人使用、在他所研究的语言的话语中正在引出新的问题和可能性的迹象。然而。对他来说,问题在于那种语言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他作为历史学家可以利用、但他研究其语言和历史的行动者却无法利用的语言那样,充分显示那种语言的历史背景的变化。对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20世纪的范畴去解释17世纪使用的范畴这一类问题,他可以迫使自己遵守一条纪律,只去解释17世纪语言的变化如何指明了历史背景的变化,它指明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什么样的变化是按指明这些变化的方式发生的。既然17世纪的行动者的语言对其历史背景做出的回应不同于他本人使用的语言做出的回应,那么在根据语境进行解释时,17世纪的言说也许远没有给他机会去利用他希望加以利用的历史解释的范畴——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机会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但是,研究话语的历史学家不能搞出一套其中根本没有的语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