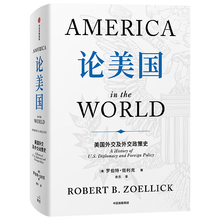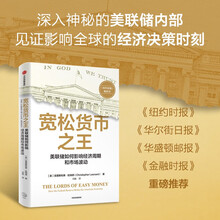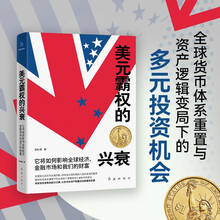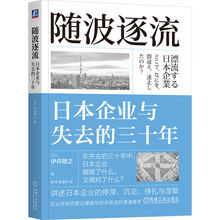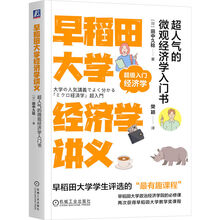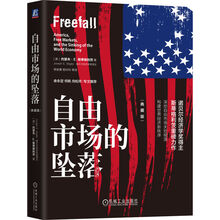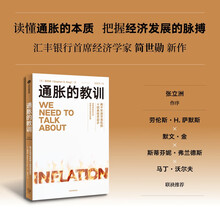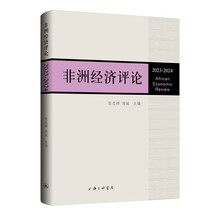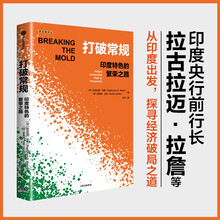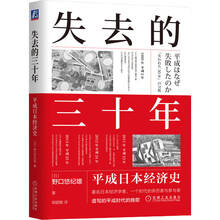第Ⅰ篇 管制与经济分析
1 管制与经济效率
管制的研究需要一个前后一致的框架。本章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个经济管制的定义。在一个市场模型里,正式的管制定义是由一系列显性关联的管制性约束得出的。因此可以按照所限制的对象(如消费者、企业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管制的分类。而且,对管制的制度和行政内容,我还强调一种实证的方法。管制的过程是由消费者和企业对管制政策及其后果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战略互动关系组成的。所以,.管制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管制下市场的均衡,也包括行政之过程。
在1.1节中,讨论是从回顾各种管制的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科学的定义开始的。我所要强调的是,虽然上述每一学科对管制特征的探究各有贡献,但传统的定义都倾向于在市场条件以外来定义管制,通常视市场为一个“黑箱”。我将在1.2节里,另外提出一个市场条件下的管制定义。
管制也许具有纯粹的再分配效果,也许会影响配置效率。因此,在研究管制时,一种规范的观点也不可或缺。在评价各种可替代的管制政策时,必然牵涉到某些比较的标准。我首先划定政府干预有可能促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的领域。当然,市场失灵本身并非管制的充分条件。正如波斯纳(Posner,1977)所指出的,“政府失灵”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替代。由政府介入其中造成资源无效配置的市场不乏其例。在运输业(如铁路、航空、货车、公共汽车及出租车)中实行进入管制即带来行业价格上升和效率降低。更毋庸置疑的是,管制常常被政府用以取得某些目的,如收入的再分配和特殊产业的鼓励,而置经济效率于不顾。许多管制措施实质上就是再分配,并且是政治过程的结果,以满足消费者或产业压力集团的自我利益。当然,管制的失灵并不一定妨碍在福利经济学范畴里进行管制的研究。通过考察最适度的管制,实际管制活动中的缺陷能够得到更好的分析和理解。如果我们将市场失灵视为建立管制制度的必要条件,我们也许能够认定某些管制不能改善经济效率的情况。
在1.3-1.5节中,我对市场失灵和相应的管制将作一番综合性的概述。我划分并定义了三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这就是分别由阻碍性交易(进入壁垒)、缺乏合法的必备条件的交易(外部性)以及产生低效率的交易权属(properties of transactions)(内部性)所造成的成本。在每一类型市场失灵之下,我都介绍了也许能改善配置效率的管制及其他可替代的社会制度。
1.1 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科学中的管制概念
在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科学领域里,管制受到广泛的研究。每一个领域都剖析了这一复杂课题的许多重要方面。早期的经济学文献所顾及的是对特殊产业或一群产业的管制。随着理论的发展,开始对可替代的政策手段的激励与福利性质作出估价。法学文献研究执法、市场规则及行政程序。政治科学的文献则把焦点放在政策形成和执行的政治及行政作用方面。正如我在阐述上述每一学科里管制的定义时所指出的,大部分讨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管制的行政方面,而置受管制市场的均衡分析于不顾。寻求一个综合性的管制定义的努力尚未结束,并受益于迄今为止所提出过的各种定义。
1.1.1 经济学中的管制定义
经济学对管制的研究已折射出美国联邦及州政府管制中广泛的重点问题。经济学对管制的理论和经验的研究兴趣曾集中于考察某些特殊产业的价格和进入的控制上。这些产业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运输)、通讯、交通(公路货运、铁路、航空)与金融(银行、保险、证券)。这种管制被称为“老式”的管制。为了体现产业研究的广泛重点,在1970年以前,管制的经济理论一般强调公共事业里的定价问题。大部分注意力都投向规模技术递增收益情况下的定价问题。讨论也都集中在如何选择能保证公用事业的资本投资有一特殊回报率的价格,以及维持成本最低化的激励等相关问题之上。为在高峰和非高峰时段最优分配消费者的需求而设计的费率结构已经运用于电力和电信产业。
管制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需要一套逻辑清晰的一般原理,以利于对受管制市场的正式模拟,并就管制制度和管制政策的后果提出某些可验证的假说。不幸的是,作为文献快速发展和变化的结果,一个具备普遍意义的可有效运用的管制定义仍未出现。为了评价和检验有关管制效果的理论,有必要对某一特殊种类的管制或某些特殊产业作详细的考据。然而,如果文献过于分散和专业化,就会出现一种危险,即每一领域里的研究者将自顾自地“重复发明车轮(reinvent the wheel)”许多次。这是早期产业研究里屡见不鲜的事情。一种管制的经济理论必须能普遍适用于可观察到的各种形式的管制活动。心怀于此,我们将回顾经济学文献中一些重要的管制定义。
直到1970年,大部分早期的管制文献都将焦点放在公用事业的管制上。体现这些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首推卡恩(Kahn,1970,1971)教授的经典教科书。卡恩(1970,P.2)将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和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y)视为两种“竞争性市场模型明显不能描述或甚至无从描述”的经济。卡恩(1970,P.20)观察到,“管制的实质是政府命令对竞争的明显取代,作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它企图维护良好的经济绩效。”卡恩(1970,P.3)对管制者对公用事业的管制作了如下定义:“对该种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的主要方面的直接的政府规定……如进入控制、价格决定、服务条件及质量的规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的规定……”卡恩的定义是建立在公共事业的管制经验之上的,并不能一般化地扩展到其他管制领域,如环境污染和作业场所安全。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作为竞争性市场内容而存在的政府制度(government institutions),在卡恩看来只游离于市场之“边缘(periphery)”,因而未作讨论。
卡恩(1970)所强调的领域主要是对垄断的管制及费率的决定。他尤其关心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原则、长期和短期边际成本及价格歧视等问题。卡恩(1971)对管制制度的考虑包括:导源于收益率管制的投入扭曲(即阿弗奇一约翰逊效应Averch-JohnsOn effect)、自然垄断与规模经济以及受管制产业(电力、电信、天然气、货运及其他)内的竞争。
谢泼德和威尔科克斯(Shepherd and Wilcox,1979,p.267)声言“管制只是管制者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管制教科书把“针对工商业的公共政策”划分为反托拉斯法、管制及公共企业(public enterprise)三类。谢泼德和威尔科克斯集中讨论的公用事业包括能源部门、通讯、运输及城市服务等。他们关于公共企业的讨论主要围绕公共所有权和对公用部门的控制。其中的重点又放在政策制定者与受他们管制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上。
1981年,一个重要的进展是由乔斯科(Joskow)和诺尔(Noll)作出的。他们全面总结了竞争与非竞争产业里的价格与进入的管制,以及对“质量”(环境、健康、就业安全及产品质量)的管制。他们还强调以管制的政治、行政程序为研究重点的管制的立法与官僚理论的重要性。
传播最广的管制定义是由斯蒂格勒(Stigler,1971,P.3)提供的:“作为一种法规(rule),管制是产业所需并主要为其利益所设计和操作的”。在他看来,管制是国家“强制权力”的运用。因此,管制几乎能采取任何手段满足某产业的欲望,最极端的就是增加它们的获利能力。斯蒂格勒列举了四项为产业所需而由国家提供的管制手段:直接的货币补贴,新进入的控制、对产业辅助品生产的鼓励及代替品生产的压抑以及价格的控制。另外,斯蒂格勒(1981)又将管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中,不仅仅包括“老式”的公用事业和反托拉斯政策,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货币筹措及支付,以及“对商品的服务和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还有法律制度。就设定一个范围或边界的意义来说,上述定义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目的。斯氏(1981)的理论偏重于管制的起源,这在管制被确切理解前是必要的。我将在下一章回过头来讨论管制的起源问题。
管制经济学家还考察过那些主要负责执行反托拉斯法的机构,即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这些研究都运用了产业组织的方法以考查反托拉斯政策对市场结构和绩效的影响效果。
自从1970年环境保护委员会(EPA)建立以来,管制的重心开始转向环境质量、产品安全及工作场所安全的管制。这种在管制教科书中能观察到的开始强调“新浪潮”或“社会性管制”的变化波及各种产业。大量有关环境管制和政策的文献开始问世,如鲍莫尔和奥茨(Balamol&Oates,1975、1979)。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关于产品及作业场所安全的文献,如维斯凯西(Viscusi,1979、1983)。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将管制研究的理论背景显著扩展到福利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科学等领域,它们都将反映在我们的讨论中。
1.1.2 法学中的管制定义
管制研究的对象是各种可替代的政府干预市场形式的复杂特征和后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既涉及市场行为的一般规则(general rule),也涉及为达到短期政策目标而采取的特殊行动。哈耶克(1960,pp.220—221)观察到,斯密(Adam Smith)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政府干预的反对尤其针对“政府强制力的使用,即非一般法的正规执行,并且迎合某些特殊目的”的现象。管制研究既包括市场的一般规则也包括随机的政策行为。
市场是一种社会习俗,而非自然现象。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掌)”依赖于管制市场交换的法律这一“看得见的手臂”。市场交换的规则一般来源于已经形成的习惯和标准的实践以及普通法。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则提供了一些附加的常常是补充性的法规,从而对交易的范围或约束或鼓励。
有秩序的市场交易对法律规则的依赖,有时被经济学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1973,第一卷,p.4)里一个主要的理论是:“律师所研究的正当行为的规则,作为一种秩序,其大部分特征都不为律师所知;而研究这种秩序的经济学家也同样不详知他所研究的秩序依赖其上的行为规则的特征。”对受管制市场的研究必须从市场规则的研究入手,这是法学和经济学的接壤之处。通过研究市场得以运转于其中的制度框架的研究,我们也许能更好地描述特殊的管制制度的效果。更进一步,我们也许可以对管制是否能促进市场配置作出估价,并且决定应该采用何种形式的管制。
人们常常认为,市场交易和市场的政府管制构成资源配置的两种可替代方法。如果我们将管制的含义限制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这并非管制的唯一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与普通法相比,管制也许能为市场交易提供一个成本更低的基础。在处理市场参与者遇到的问题时,管制不必拘泥于命令和控制的传统形式。行政管制能够借助普通法的形式和程序。管制也可建立允许市场式配置机制运行的规则。除此以外,管制机构可建立一种法庭(forum),使特殊权力得以实施;与此同时,某些判例(precedents)也被建立起来,以避免特殊结果和配置的出现。因此,管制论者必须证明,与司法执行规则相比,公共管制所提供的规则,不但能降低行政成本,而且能带来更有效的资源配置。
对合约安排的干预是否必要,是管制中涉及到的重要问题。如果个体代理者选择自愿的交易,私人间的谈判应该产生有效的配置。另外,合约的形成,是合同法、财产法和民法等普通法的管辖对象。任何对管制制度是否必要的估价,都必须考虑可替代的法律制度。例如,通过对产品和作业场所安全的管制而取得的市场配置,就必须与义务规则(liability rules)下能观察到的市场配置相比较。因此,管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要涉及可替代的法律制度的研究。
管制中另外一个基本问题是要分清执行一般规则和特殊限制的方法。许多这样的问题在法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了处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规则是否应该通过公法或私法的努力去执行。行政管制的作用也许与来源于公法执行的正的净利润相关。
合同、民事及财产的普通法一般都通过私法来执行。正如兰德斯(Landes)和波斯纳(Posner)(1975,p.3)观察到的,“国家的作用仅限于提供一套法院体系。”刑法大部分是公法执行的。反托拉斯法则代表一种公法和私法混合执行的有趣形式。三重损害惩罚(trebledamages penalty)为私法执行提供了激励。管制机构或依赖私人控诉,或依赖信息收集中发现的有关违犯产品质量标准和作业场所安全规则的犯罪报告。个人向管制机构提供信息的作法,体现了私法和公法执行的相互结合。
对公法和私法执行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献日益增多。在一篇重要的论文里,贝克尔(Becker)和斯蒂格勒(1974)认为,竞争性的私法执行通过来源于罚金的激励,能够取得最佳的执行效果。兰德斯和波斯纳(1975)对此有歧义,他们指出,通过高于外部损害水平处以罚金和降低拘捕的可能性,公法执行能够在更低的成本之下实现。然而,在更高罚金的情况下,私人部门将增加执法资源的投入,从而导致无效率的过度投资。波林斯基(Polinsky,1980)指出,刑事犯罪会引发外部性损害。在此情况下,由于有限损害(各个违法者造成的损害其实是可加的),私法执行会导致投资不足。波林斯基声称,竞争性的私法执行成功率不如公法执行。因此,即使公法执行在成本上不占优势,从社会角度看却更为可取。
法律的执行,除了具备公共商品的性质,也可能存在规模经济性。从单个原告的角度看,法律的诉讼成本可能大大高于其所受到的损害,虽然所有原告所受的总损害大于一次法律诉讼的潜在成本。波斯纳(1977,p.449)指出,一种集团诉讼将许多零碎诉讼汇集起来,能够产生诉讼的规模经济。但波斯纳又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原告所受的损害较小,而原告的数量却很多,则使每一个原告得到赔偿的成本会高得令人咋舌。可是,如果无法提出集团诉讼,那么,社会就不能享有对违法者处以罚金而产生的预防效果所带来的利益。
行政机构扮演的角色是,将个人的申诉汇集起来,并根据来源于个别消费者的申诉,对违法者处以赔偿性处罚。与集团诉讼不同,所收到的申诉不一定来源于同一时期,但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另外,管制机构可以根据少数申诉展开自己的调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