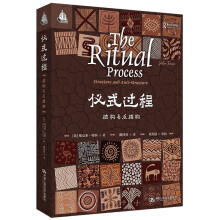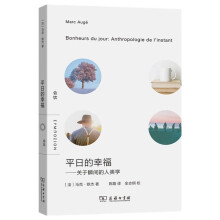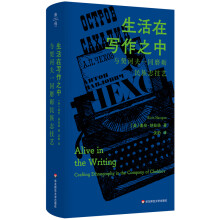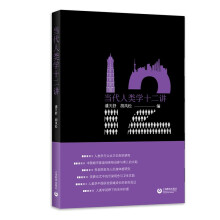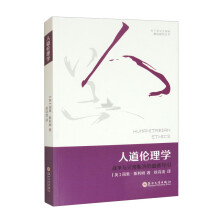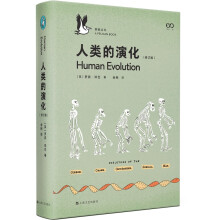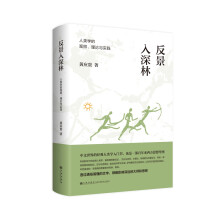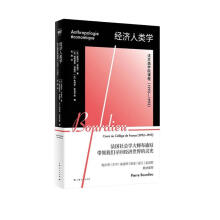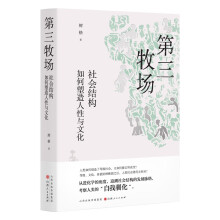与恩格斯等人的语焉不详相比,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其理想社会中男女关系的描述则非常清晰。在现实的希腊诸城邦中,最合柏拉图心意的,是斯巴达。
在古希腊人眼中,斯巴达无疑是个另类。它先是征服了拉哥尼亚人,使其成为斯巴达的公有奴隶,即黑劳士。接着又征服了美塞尼亚,给予其居民很少的财产权和生命保障,其境遇比黑劳士好,但很有限。斯巴达人把美塞尼亚人布置在自己与黑劳士之间,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要知道,黑劳士人数是斯巴达人的7倍,在冷兵器时代,这显然是个致命的优势。事实上,斯巴达日后也正是毁于国内奴隶的反叛,而不是外族的入侵。就这样,斯巴达人虽免于劳役之苦,却一直生活在惊恐之中。传说中伟大的立法者吕库古,为危如累卵的斯巴达人设计了一套古怪的制度,以保证斯巴达的长治久安。从斯巴达生存的时间及其在希腊诸城邦的地位来看,这套制度应该可以打85以上的高分。
首先,在政治方面,全体斯巴达人平等享有公民权。名义上,最高权力归于全体公民大会,但是提议案的权力却掌握在30人元老院手上。更糟糕的是,表决的时候并不计票,而是与会者发出喊声——喊声是否大到足以通过某议案,由元老们判定。所以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寡头体制。因为,如果你对某提案感到不满,你的权利仅限于不喊。而在经济方面,吕库古规定禁止使用金银,改用铁币。价值10明那的铁币,得用两头牛才拉得动。为了防止有人拿一堆钱锻把锤子或犁,铸币时特意加了道工序:蟀火时用醋浸一下,让钱变得脆而易碎。斯巴达男人终生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训练和战斗。每个男人从18岁起就要到公共食堂就餐,粮食从家中自带。如果哪个男人穷得连公共食堂的份粮都交不上,其公民权就会被暂时终止。伙食很差,一个叙巴里斯人在公共食堂喝了一口黑扁豆汤之后说:“现在我知道斯巴达人为什么不怕死了。”这样的日子,斯巴达男人一直要过到60岁。
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很高,虽然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投票,但是她们有财产继承权。在亚里士多德时代,2/5的土地掌握在女继承人手上。与其他城邦不同的是,斯巴达少女也要接受体操训练,训练的时候与男孩子一样赤身露体。平常她们穿着半长袍,两侧开叉很高。斯巴达女人因而得了个外号——露大腿的人。事实上,她们连屁股都露得出来,因为那时候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内裤。虽然有婚姻制度,但是如果李四看上了朋友张三的老婆,可以大大方方向张三提出要求。这种要求近乎我们今天“哇,张太太好漂亮”的恭维,让张三夫妇心里很受用,所以通常都不会拒绝。
柏拉图虽然不喜欢斯巴达的寡头制,却更加痛恨雅典浅薄的民主制。在他的《理想国》里,简直就是为能征善战的斯巴达人度身订做了一个角色,叫做“护卫者”。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私心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城邦的忠诚。要想杜绝私心,显然就要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所以在他的“理想国”中,护卫者只能拿工资,用于日常支出,但不能拥有不动产。进一步,为从根子上打消护卫者们攒钱的动力,以及出于优生优育的考虑,柏拉图主张通过“巧妙的抽签”来剥夺劣等男人的生育机会,“以使不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能怪治理者”。而被选中的好男人和好女人,则分别在“从过了跑步最快的年龄到55岁”和“20岁到40岁”期间,尽量为城邦多生孩子。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到托儿所,由专人负责照料。在母亲有奶的情况下,托儿所的负责人“引导母亲们到托儿所喂奶,但竭力不让她们认清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来,不仅父亲的身份被混淆,连母亲的身份也被混淆了。
这个设计的麻烦在于:万一父亲与亲生女儿、母亲与亲生儿子,或者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之间发生了关系,岂不糟糕?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给出的办法是:父母一辈结合后7到10个月内,社团内所有生下的孩子都算是下一辈,上一辈不得与下一辈有性关系。考虑到人群中的年龄是一个连续的过渡,而且人是天天做爱的,并不像鹿那样一年只发情一个月,所以按这个办法划分辈份实际上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柏拉图的这个设计还不如前文所述的澳洲土著的婚级制:他们生而有标明自己婚级的名称,正如中国人家谱里给每一辈泛个字那样,男女各分四级:在男子,分别为伊排、孔博、慕里和库比;在女子,分别为卡波塔、玛塔、布塔和伊帕塔。所有的伊排与所有的卡波塔互为婚配,与其他的则被禁止。余此类推。
在柏拉图的设计中,父母双方的身份都被混淆了,所以平辈之间也无法避免亲兄妹之间发生性关系。这又怎么办呢?柏拉图的回答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而德尔斐神谕又允许的话……”可见是在捣糨糊。当年诗人维吉尔和朋友共享一个情妇,这个情妇还给他们生了个女儿。女儿长大后,维吉尔和他的朋友轮流和他们的女儿睡觉——今天和维吉尔睡觉,就管那个朋友叫爸爸,次日再换过来。要知道,德尔斐神谕并不比轮流叫爸爸更靠谱些。
虽然柏拉图的具体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对抗家庭,社团就必须财产公有并打破血缘关系。史上最成功的社团,当推寺院。修道院也好,庙也好,都是财产公有并誓守独身的。
柏拉图之后,认为私有财产乃罪恶之薮的人、反感家庭的人,提出了种种设想。《乌托邦》虽然很有名,但今天看来简直就是笑料。托马斯·莫尔虽然主张财产公有,却并不反对家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