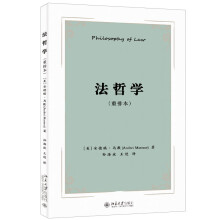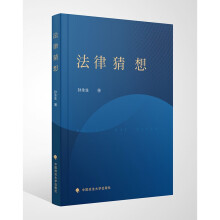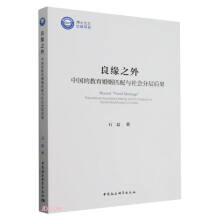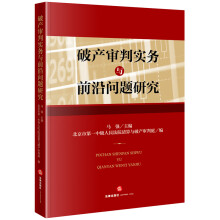精彩书摘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些接连不断的救亡的燃眉之急,要求把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起来,因而集体主义便代替了个人主义,专制强权最后淹没了知识分子对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如果我们看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史,这种说法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这种解释最大的困难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存在亡国危险,“救亡”是一百年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不能仅仅把这个现象用于191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对军绅政权的不满和批判,以及对社会整合危机之焦虑,正是新文化运动之推动力,亦即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提倡启蒙本身正是出于救亡的需要。救亡压倒启蒙说不得不面临一个二律背反:“救亡”既然导致早期的“启蒙”,为何又会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中断“启蒙”?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就始终存在“救亡”意识,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至于辛亥共和革命,都是因“救亡”而作出的反应。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救亡危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更为迫切。为何独独在这时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说法的毛病在于,它忽略了在“救亡”的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变迁还有自身的内在演变机制和路向,“救亡”是通过对旧意识形态的抛弃而和“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任何一种带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或潮流中,“救亡”都是最具动员力量的,它确实可以推动某些观念兴起,使某些价值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仅仅有“救亡”的动员力量,不一定导致价值独断。正如辛亥革命期间,反清排满、共和也是出于“救亡意识”,但民初时并没有因之而出现某种价值独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