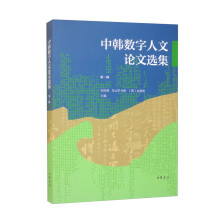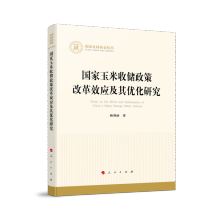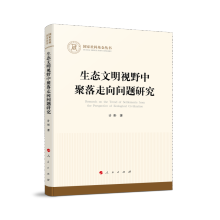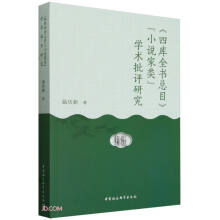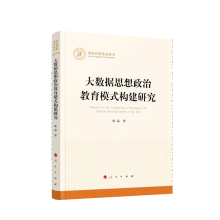这段话里面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方面。其一是伦敦用了两组对立的比喻:肉体和精神,野蛮人和圣人。很显然他所谓的“两种本性”,一方是指内心比较现实的“我”,是个追求肉体感觉的“野蛮人”;另一方是文本中和想象中塑造的“我”,是个崇尚精神的“圣人”。这显然是自我的分裂。其二是他最终能够达到平衡的结论。作家意识到,这种分裂人格是造成“麻烦”的根源,但是我们对“取得平衡”之说不敢轻信。倒是他的小说反复地将他本人性格中的冲突戏剧化了:对立的两方--一个鲁莽的冒险家和一个带书生气的敏感青年;一个追求金钱的“脑力商人”和一个追求艺术理想的作家;一个大言不惭的个人主义者和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社会主义者--在每一方面都遭遇了分裂自我的另一半的挑战,互相角力。我们发现,各种感情倾向也以一组组对立的意象出现在杰克·伦敦的作品中:城市与乡村,工业化与田园,文明与荒野,弱者与强者,男性代表的强悍与女性代表的教养,有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物质与精神,成功与幻灭,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平衡完整的自我是一种很难企及的境界,杰克·伦敦声言的“达到”,主要是一种幻觉。由于人的欲望与现实提供的可能性之间永远存在着鸿沟.欲望永远无法完全满足,因此人的自我本质上是缺损的、失衡的,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加以调整修补。现实中杰克·伦敦的真实自我是残缺的,他通过文学文本建构了一个虚构的自我,创造平衡,使之更符合心理期待。这样,在杰克·伦敦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作家本人的影子,即所谓的“野蛮人”和“圣人”。自我的一方追随当时的流行风尚,为物质利益不择手段,写最能卖钱的小说,当“脑力商人”;另一方则想象着事物原本可能达到的美好,感受到强烈的道德危机,而焦虑又使他对现实不满,于是扯起了批判的大旗。就这样,一个不顾一切的实利主义者,和一个呵斥实利主义行为的道德家,就可能出现在杰克·伦敦的同一个小说人物身上。对于杰克·伦敦来说,他的文学话语既是调和欲望和现实之间矛盾的产物,也是分裂自我的见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