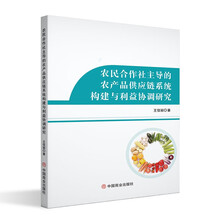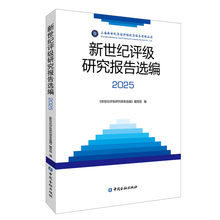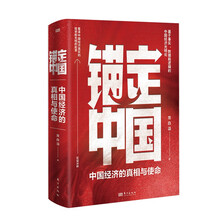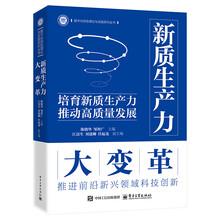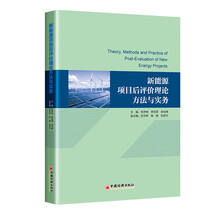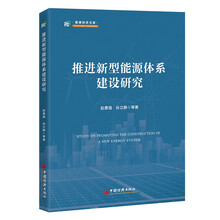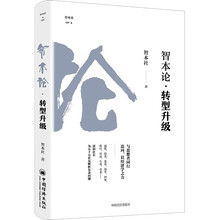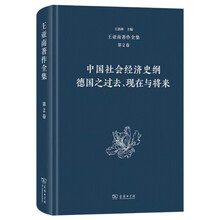这本书从1996年10月接受任务算起,到今天(2000年6月3日)终于杀青,已经三年多了。尽管正式动笔是在去年8月,但这三年多来,却是在兹念兹,寝食不安。整个写作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先是在赵德馨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拟定全书提纲,到1997年4月敲定提纲,其间三易其稿,历时半年。随即进入第二阶段,研读近十年来刊布的近百部论著和上千篇论文。这是因为笔者十年前写过一本《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对十年前的研究状况比较熟悉的缘故。研读中我逐步认识到,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为此必须回到史料中去,重读宋、辽、金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和宋人文集、《全辽文》、宋元方志等基本史籍,通过认真梳理材料,方能真正消化学界成果。所以这个阶段原预计半年,结果拖成两年,当然其间所任行政事务也耽搁了部分时间。这样,直到去年8月暑假中才进入动笔阶段。在动笔写作的十个月中,没有双休节假,不分白天黑夜,除了上课开会,就是伏案写作。每天以平均2000字的速度向前推进,经常写到凌晨二三点钟才搁笔。孤灯一盏,清茶一杯,万籁俱寂,心无旁骛,惟有思索在头脑中来回穿梭,变成一个个判断、论点、认识和心得体会,潺潺流淌在洁白的稿纸上。<br><br> 今天回头来看《宋辽夏金经济研析》这本十年前的处女作,疏漏、失误之处所在多有。近十年来,想要重新修订这本书的愿望时时萦绕在心头,而且随着卡片的积累、读书的增多以及认识的深化,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感谢赵德馨教授主编这套《中国经济通史》,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重拾宋辽夏金经济运动这个重大课题,得以多少弥补一些那本处女作中的诸多失误和疏漏。<br><br> 当然也得承认,本书在价值取向、学术路数、思维脉络、基本观点,乃至框架结构、表述方式等方面,与前书仍有“割不断,理还乱”的种种关联,特别是在基本思路上仍是一脉相承的。笔者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下几点:<br><br> 一是强调整体性观念,即将宋、辽、夏、金各区域政权作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经济整体来考察。因此本书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经济区域。除最后一章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专门分析外,对辽、夏、金等辖区的经济考察同样贯彻了这个原則。如辽朝辖区可分南部燕云农业区、中部契丹腹心区和西北部族游牧区;西夏可分兴灵平原(即黄河前套)腹心区、宋夏沿边交界区和河西走廊这样三类地区。这样做是为了突破朝代经济史的局限,不仅看到中原经济区和江南经济区的区别和联系,而且看到周边游牧经济区与中原、江南农业经济区的互动和影响,使本书真正成为断代中国经济史。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是由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并立政权共同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将宋、辽、夏、金纳入同一经济圈进行考察,许多单从一个朝代来看难以圆满解释的问题,才能得到新的观察视角,给出合理的解释。本书第一章关于10—13世纪中国经济运动的时代特征,就是在整体性观念下得到的认识。这些特征在当时经济运动的各个侧面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书各相关章节已有述及。<br><br>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能不能把宋辽夏金的经济运动视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如前所述,宋辽夏金各个辖区自秦汉隋唐以来一直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而且在北宋实现局部统一后。由于政治壁垒的消除,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以及草市勃兴、市镇网络出现和区域市场的形成等等原因,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前更为紧密,人员和物资交流的规模也更加扩大。在10世纪以降的三四百年中,中原地区的数百万劳力资源向江南经济区移动,又有数十万汉族百姓自愿、非自愿地流入东北、内蒙甚至新疆地区。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粮食、布帛乃至巨额铜币源源不断地输往汴京、河北、陕西。以至党项、契丹和女真故地。在汉族农业经济和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契丹、党项、女真等周边部族相继步入封建化行程。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当时宋辽夏金各辖区通用同一种货币,是北宋三亿多贯的巨额铸币为这个货币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事实说明,宋辽夏金各个辖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具有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某些要素。19世纪中叶,恩格斯曾说当时的英国是“工业太阳”,而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其他民族国家则是围绕英国转的“农业卫星”①。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在10--13世纪,宋朝(特别是北宋)是处在中心地位的“农业太阳”,而党项、契丹、女真、回鹘、吐蕃等周边部族,则是围绕宋朝旋转的“游牧卫星”。至少从经济角度看是这样。<br><br> 二是强调宋辽夏金时期的经济运动受到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除了地主与农民这对矛盾外,本书特别关注因受第三寒冷期的影响而突出起来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以及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对商品经济的制约这两个重要矛盾。笔者认为当时经济运动的轨迹处处受到上述三个基本矛盾的影响和左右。例如宋朝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赋入丰赡.却以“积贫积弱”而著称(此因游牧经济板块的强烈挤压,宋朝只得“以兵为险”,军费开支浩瀚之故);北宋原始工业化进程启动,都市化进程加速,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却未能加速近代转型的步伐(此囚专制集权体制压制近代化组织因素的成长)等重大问题,其谜底即隐藏在这三大矛盾之中。他如行会被官府用作控制和榨取工商业阶层的工具,纸币被政府作为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的手段,以及政府垄断型货币投放体制导致“钱荒”等等,均与专制集权体制的弊端有关。当然,这些认识是否尚有些许道理尚待学界的评判,笔者不敢自以为是。<br><br> 三是本书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当时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上面。着力揭示的是当时经济运动的脉搏、轨迹和演进方向。为此或列专章、或以专节专门讨论这300年间农耕线向东南方向的持续收缩,农耕区向东北、内蒙地区的波浪式推进,黄河流域牧业经济比重的明显上升,以及土地私有化潮流、原始工业化进程、都市化进程,还有摊丁入亩趋势这样一些带规律性、趋势性的问题。本书引用史料是为说明问题,而不以史料罗列为长。这既是本书的长处,恐怕更是本书的短处。正像人们对商品有着经济学意义上的“偏好”一样,学术上的不同流派也会有不同偏好,殊难一概而论。<br><br> 四是本书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认识、判断放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为此笔者引用了上百种历史典籍,参考了数百篇中外学者的学术论文,也没有放过文物考古资料所提供的宝贵实证。例如近年来宋代汝窑遗址在河南宝丰县的出土,秧马实物在江苏镇江农村的发现,以及日本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掘等,都是本书立论的重要依据。<br><br> 我在拙著《中华文化通志·土地赋役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说过如下一段话,移录于此作为全书的结尾:<br><br> 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一书的“初版序言”中说:“这部书稿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十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这也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没有海内外诸多学者数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和扎实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本《土地赋役志》(此处应换成《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一书)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在此,谨向许多给予我启发、教益的师友和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br><br> 葛金芳<br> 2000年6月3日凌晨草于武昌沙湖之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