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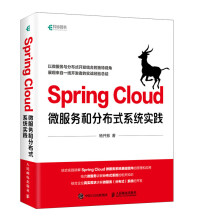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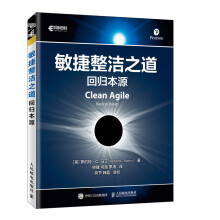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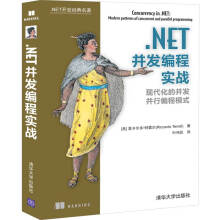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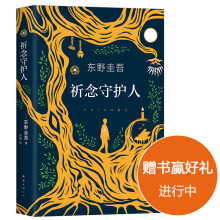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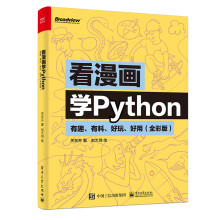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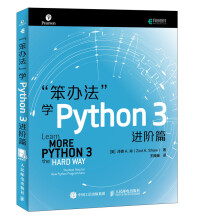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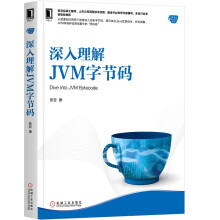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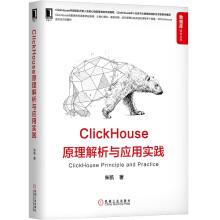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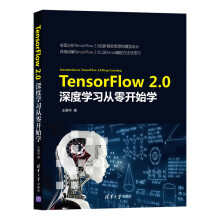
◆中西诗心的跨时空对话:以钱锺书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为核心,深度解析其如何通过《管锥编》《谈艺录》等经典著作,在文学、哲学、历史等多领域展开对话,揭示人类文化共通的审美规律与精神内核,展现“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学术洞见。
◆解构传统,重释经典:聚焦钱锺书对阐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现代西学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以“现象学式话语空间”为方法论,重新激活中国传统典籍的现代意义,呈现经典文本在当代学术中的鲜活生命力。
◆从“钱氏范式”看学术突围:钱锺书以跨学科视野破除理论桎梏,通过中西文本的自由对话,在具体比较中揭示人类审美共性。这种不依赖体系建构却直指本质的研究路径,为当代人文研究提供了突破边界的创新范式。
编辑推荐
◆中西学术的交汇与重构:本书以宽广的学术视角,深度展现了钱锺书如何通过中西文化的深度对话,开创独特研究范式,重构现代学术版图。书中通过剖析《管锥编》《谈艺录》等经典文本,揭示了钱锺书如何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实现理论创新。
◆跨学科研究的典范:钱锺书以融贯中西的学术视野,解构了学科壁垒。从阐释学到形式批评,从心理学到比较文学,本书全面再现了钱锺书在多学科领域中实现理论创新的学术图景。
◆学术方法论的启示:从“打通中西”到“现象学式话语空间”,钱锺书的学术方法论不仅突破了传统学术的局限,更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书通过具体的研究案例,详细展示了钱锺书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学术研究方法,为当代跨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
◆全球学术视野中的钱锺书:钱锺书学术思想兼具本土深度与全球视野,不仅浸润中国学界,更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引发持久共鸣。此次再版新增《鉴画衡文 道一以贯》《“世界的钱锺书”与“钱锺书的世界”》两篇长文,以“钱氏范式”为学术棱镜,全面揭示其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和意义。
《钱锺书与现代西学》以钱锺书学术思想与西方理论的深层对话为核心,通过阐释学、解构主义、形式批评、比较文学、心理学、新历史主义六大维度,系统剖析了钱锺书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处构建独特的话语空间。全书以《管锥编》《谈艺录》等经典著作为基础,揭示钱锺书突破学科藩篱、融通古今的学术路径:他既以中国传统诗话的“擘肌分理”为根基,又借镜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现象学式观照,在“阐释的循环”中深入剖析中西诗学的共通文心。
书中特别强调钱锺书对诗史互证、通感、翻译的化境等命题的创造性阐发,展现其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广阔视野,将禅宗妙悟与解构思维、形式批评与心理分析熔铸一炉,形成独特的学术气象。全书不仅追溯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还通过双向互动的学术史视角,揭示其如何以现象学范式重构离散的文化碎片,最终形成超越逻辑体系的互文性阐释场域。
钱锺书对“和而不同”对话原则的实践,不仅为当代人文研究提供了跨文化阐释的典范,更为全球学术界贡献了独特的中国视角,其学术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深度对话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围城》
一般而言,人们总喜欢把《围城》称作“学者小说”或“学人小说”。从作品中纷至沓来的比喻、俯拾即是的典故来说,可以说名副其实。但从钱锺书本人来说,却“毫不领情”,因为他对所谓学人之作颇不以为然。早在《谈艺录》中,他就对学人之诗颇有微词,到《管锥编》中更是明确标立“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词人体察之精,盖先于学人多多许矣”、“诗人心印胜于注家皮相”,等等,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
对于钱锺书来说,分取创作与学术两途,是要在不同的领域尽情施展身手,两者虽有互文相通,却不可等量齐观、合二为一,成为什么学人小说。或许可以说,钱锺书是想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解构一下“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显示身兼学人与文人双重身份的可能性。从《围城》本文来说,处处自觉不自觉地流溢着钱锺书丰厚的中西文化素养,却又似蜜蜂以兼采为味,无花不采,吮英咀华,滋味遍尝,取精用弘,“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明明是舞鹤,却只见舞姿而不见鹤体,“体而悉寓于用,质而纯显为动,堆垛尽化烟云,流易若无定模”,全销材质于形式之中,文成而不觉有题材,全然没有学人之诗的迂腐与无味。因此,与其说《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不如说它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型文本。
《谈艺录》
《谈艺录》以传统札记形式写成,标立为九十一则正文及二十四则附说,一九八四年的补订本篇幅上又扩充一倍。所论述的内容非常广泛,以诗为主,而兼及其他各种艺术门类;以文学为主,遍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领域;以唐宋明清为主,又上溯先秦,旁及中西古今文化。全书以“诗分唐宋”开篇,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与中西诗学理论研究为两大并进线索。
《谈艺录》具体鉴赏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在中西不同的诗学语境中,阐述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为此,《谈艺录》在继承传统诗话的同时,又引述了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各家之说,融合了现代西学的方法与理论,从而将中国传统诗话推向了顶峰。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终结,也为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一个典范。应该指出的是,《谈艺录》初版本只代表了钱锺书的阶段性成就,只有在《管锥编》及《谈艺录》补订本问世之后,《谈艺录》才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并与其他著作一起,汇成了钱锺书著作充满张力的话语空间。
《宋诗选注》
选诗方面钱锺书则独标“六不选”原则。这是他对古典诗文选学的贡献,也代表了钱锺书对宋诗的态度: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蒙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末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六不选”原则为《宋诗选注》提供了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作家作品的选择出现了较大的升降,并以具体鉴赏、阐释为基础为每个诗人重新定位。所选的八十位诗人中,既有王安石、苏轼、陆游等大家,亦有吴涛、乐雷发、利登、洪炎等名不见经传的“新人”,颇有“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之势。
《管锥编》
钱锺书晚年的集大成之作显然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奇书《管锥编》。它的完成使得钱锺书的话语空间最终得以确立,并跃上一个全新的境界。如果说此前钱锺书的全部著作还基本停留于谈艺论文,寻觅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那么到《管锥编》中则上升到了文化思想层面的跨文化研究,对人类文化展开了整体批判。《管锥编》评骘了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融经史子集于一炉,几乎囊括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即便如此,已经出版的《管锥编》还只是初辑,“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这样气魄宏大之作,却被钱锺书命名为“管锥编”。“管锥”二字语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这种含义也体现在他所认可的英译书名中:“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 “管锥”二字充分显示了他的谦逊,也显示了他对人类知识话语丰富性的尊重。
《管锥编》植根华夏,融化中西,或论史,或衡文,或点化,或评析,钩玄提要,触类旁通,察一于万,又寓万于一,在评注古籍的外衣下,孜孜以求地探究与抉发出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显现出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全书涉及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西方语文,旁涉文学、史学、心理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人文学科。它树义警拔超绝,论述横扫六合,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在学术层面与思想层面上都有着无穷的创见,卓然而成一家“钱学”。它没有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演绎的体系构造,而是突破学科与中西藩篱,将异时异地相统一的观念,非历史性地捉置一处,推源溯流,探本求末,交互映照,从而达到对超时空的绝对观念的契悟神通,进入人类文化反思的更高境界。
和而不同
钱锺书坚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散为万殊,聚则一贯,中西文化虽然思想方法、话语模式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的“理”则基本一致。此“心”之能“同”,同于此“理”;此“理”之能“同”,同于此“物”;“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水性如一,故治水者之心思亦若合符契。……思辩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所以,钱锺书始终面对的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解构。他在对中西文化的解构中探源溯流,洞幽烛隐,破解话语,贯通衔接,抉发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希求别创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生面。文化因子,吸收了中外有益生动的文化精义,融汇中西,打通古今的崭新境界,充分体现了钱锺书卓越的文化史识。它也再一次证明,解构不是简单地对结构的分解,对体系的破坏,并不仅仅意味着击垮系统,而且意味着“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成是凝聚起来的可能性,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这种开放性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其实已经涉及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为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思考文化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尺度。借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一个术语,我们也可以说,钱锺书所关注的正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商讨和杂交性。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商讨不是绝对的对某一方的否弃,而是将对立或矛盾或统一的成分予以会通。它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是势所必然的,这种碰撞无论是敌对性的还是互补性的,都是一种话语实践。它们在表征层面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决不能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中的既定的种族属性和文化属性,因为文化差异的社会表现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持续不断的商讨行为。我们应该放弃普遍化的认同,而寻求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相对认同;不一定要扭曲自我的文化,一味地去求得全球化的虚假的认同,“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和而不同,应该是多元文化时代中我们应有的文化认同策略。
史蕴诗心
谈到诗与史的关系时,曾明确批评“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只知诗具史笔,不解史蕴诗心”的现象。钱锺书关注的是史蕴诗心,是历史叙事中的文学性因素。他指出历史叙事中“不乏弄笔狡狯处,名以文章著者为尤甚。虽在良直,而记言记事,或未免如章实斋《古文十弊》之三所讥‘事欲如其文’而非‘文欲如其事’。……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历史叙述中充满了文学的想象力,“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历史叙事的文学想象力中外皆然,“十六世纪锡德尼《原诗》早言:史家载笔,每假诗人伎俩为之;希罗多德及其祖构者叙述战斗,亦效诗人描摹情思之法,委曲详尽,实则无可考信,所记大君名将辈丁宁谕众之言,亦臆造而不啻若自其口出尔。十九世纪古里埃论普罗塔克所撰名人传记云:‘渠侬只求文字之工,于信实初不措意。为琢句圆整,或且不惜颠倒战事之胜负’”。钱锺书的这些论述,让我们再次想起了海登·怀特的论断:“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世界历史叙事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我们在叙述历史时依靠比喻的语言来界定我们叙事表达的对象,并把过去事件转变为我们叙事的策略。历史不具备特有的主题;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种样子而使用的诗歌构筑的一部分。”我们以往只是把历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性表述,却忽略了历史叙述中无处不在的想象性的、虚构性的因素,正是这些构成了“历史的文本性”与历史的诗心文心。
绪 论
一、双向互动的学术创作历程
二 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
第一章 阐释的循环:钱锺书与阐释学
一、语言、训诂与阐释
二、作者意图与主体参与
三、通观圆览与共味交攻
四、循环无穷的阐释境界
第二章 解构之维:钱锺书与解构主义
一、拆散破碎与“洋葱头”
二、以言消言的立场
三、解构与建构
四、不同话语的自由穿梭
第三章 文本·形式·细读:钱锺书与形式批评
一、从俄国形式派到新批评
二、陌生化原则
三、语境与含混
四、意图谬见·悖论·细读
第四章 跨文学与跨文化对话:钱锺书与比较文学
一、超迈前贤的卓识
二、比较诗学
三、翻译:跨文化传通
四、比较文化与文化对话
第五章 探究心理的世界:钱锺书与心理学
一、心理学:学士不如文人
二、梦的解析
三、创作的心理流程
四、感觉情绪挪移与文学情境
第六章 文学与历史的辩证:钱锺书与新历史主义
一、历史:想象性的叙事
二、文学与历史的互通
三、史蕴诗心
四、“六经皆史”辨析
附 录
鉴画衡文 道一以贯
“世界的钱锺书”与“钱锺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