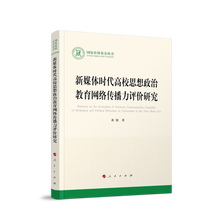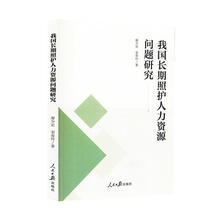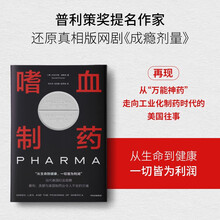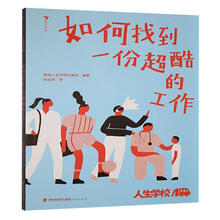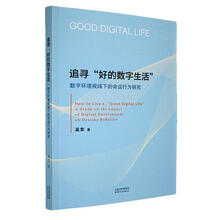导论篇
**章 导论
田野工作是什么?田野工作有什么意义?田野工作的性质和目标又是什么?田野工作中的情感和伦理等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困扰田野工作者但又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一、田野工作的含义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field work的直译,也可以称为“实地工作”或“实地调查”“实地考察”“现场调查”等。
简单来说,田野工作就是研究者离开书斋到实地或现场中去,通过观察、访问等方式搜集和分析**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进行详尽的描述,以求准确理解或解读研究对象的人文世界的一种社会研究方式。
田野工作是现代人类学区别于古典人类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古典人类学或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书斋”式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因此,古典人类学家往往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例如,弗雷泽编著的《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就是利用世界各地奇风异俗的文献资料汇编起来的。早期的西方人类学家大多足不出户,他们依据文献资料或传教士收集的各地文化习俗资料来研究文化。
**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等人离开欧洲,分别乘坐轮船到达遥远的大洋洲,以及印度洋上的一些岛国并进行调查,开创了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现代人类学,实现了古典人类学向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20世纪初期的西方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逐步形成了现代人类学的传统:一是延续文化特别是异文化研究的传统;二是确立了文化的整体观(或全貌式观察、全景式描述)、相对观和比较观(延续了古典人类学传统);三是参与观察法(或局内调查法、主位研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现代人类学区别于古典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四是文化“深描”、“地方性知识”与“写实”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显著标志。
人类学家M. 福斯特(M. Foster)和V. 肯珀(V. Kemper)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主要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原始民族或简单社会。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转入研究有文字记载的乡民社会。例如,林德夫妇(Robert Lynd and Helen Lynd)的中镇调查(1920 年)、葛学溥(D. H. Kulp)的广东凤凰村调查(1925年)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1936 年)等。
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人类学家对非洲城镇的调查,开创了人类学研究现代都市社会的新局面。
总体上看,这三个阶段基本上是遵循“初民社会”—“乡民社会”—“市民社会”的“文明”标准来划分的,但其背后的动因则是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服务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新兴民族国家的*立与崛起,迫使西方人类学家回归本土社会研究,并反思那些从非西方社会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能否运用于西方国家本土社会或本国边疆及边缘社会的研究。其结果,是促进了反思人类学的产生和人类学新理论格局的形成。[1]
无论人类学研究的场域怎样转换,也不管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如何发展,文化与异文化、观察与参与观察、访谈与深度访谈、民族志研究以及整体观、比较观和相对观等核心概念,共同形塑着田野工作的本质内涵。
二、田野工作的意义
田野工作对于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十分重要。可以说,没有开展田野工作,就不能称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另外,随着田野工作方法的发展和日趋成熟,它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质性研究。
(一)田野工作是现代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典人类学一般没有实地调查,即便有一些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也没有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所强调的全面、细致和深入。虽然古典人类学家埋*书斋里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类似于现代人类学的“文献中的田野”,但古典人类学依然是客位的、他观的或“局外人”的研究,而现代人类学则强调主位的、自观的或“局内人”的研究;二者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也不相同,前者缺乏整体观、相对观,只强调比较观,后者则强调整体观、相对观和比较观的有机统一。
(二)田野工作是获取质性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
田野工作是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和*基本的方法。它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2],是民族志(ethnography)作品的构架源泉。“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开始了田野工作。”[3]只有深入研究对象所在的社区,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谱系调查、住居体验等方式,才能全面、细致、系统、深入地收集**手资料,才能了解当地人头脑当中的“文化地图”,才能正确地获得“地方性知识”,*大限度地避免“文化误读”,进而为民族志研究的“文化深描”奠定厚实的资料基础。
(三)田野工作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来源
田野工作虽然来源于人类学研究,但它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学学科,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其他学科。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利(Bailey)在其《社会研究的方法》第十一章“人种学方法论”中,认为“人种学方法论收集资料的重要手段是观察”。[4]这里的“人种学方法”主要是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5]
实际上,在质性研究方法中,观察与参与观察、访谈与深度访谈、个案或案例研究、制度分析乃至扎根理论研究,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开展田野工作,才能全面、准确、科学、规范地收集到**手资料,并通过“主位 + 客位”的研究立场以及主位—客位—“主位+客位”—客位的研究者角色转换,获得对研究资料的深度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解读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理解其社会制度、社会行为或社会实践,进而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田野工作中的观察与参与观察、访谈与深度访谈本身,又构成了个案或案例研究、制度分析乃至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的资料收集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工作构成了质性研究方法的方法来源。
三、田野工作的性质
当今世界的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科技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已经大大缩短了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这些事实推翻了来自西方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事实上,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和研究对象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文化的表述者。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核心,也是人类学学科的鲜明特征。它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当然,它也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田野工作,它强调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但它的归纳、演绎与推理并非像自然科学那样呈线性的,更多是非线性的;它的哲学基础是人文主义的,而非实证主义的。尽管它在现代人类学产生初期曾试图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全面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研究”,但它依然无法摆脱人文主义的传统,以至于它后来逐渐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转变。这种转变使其学科定位和学科边界趋于模糊。如今,人类学的人文主义倾向和阐释学味道越来越浓,其研究范式从写实民族志向实验民族志转变、从单一民族志向多点民族志和全球民族志转变、从现实民族志向虚拟民族志转变。人类学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在地研究+全球视野”的研究范式,强调人类学研究虽然是在某个“地方”上展开,但其研究视域则是超越地域社会的。正是这种超越地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赋予了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学科特色,即微观世界里的宏观思考与分析。
作为文化理解方法的田野工作,它强调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的有机结合。特别是运用主位研究方法收集资料,用主位研究方法+客位研究方法分析资料,以寻找到研究对象头脑当中的“文化地图”,并借由该“文化地图”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社会文化的深度理解和文化解释。在此基础上,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研究对象的人文世界。当然,“讲故事”只是田野工作者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文化深描”,它只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工作,而非它的全部。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不仅需要讲好田野工作中的“故事”,还需要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讲好“道理”,并将“讲故事”与“讲道理”完美地结合起来。“讲故事”主要运用的是主位研究方法,“讲道理”则主要运用客位研究方法,强调“文化是制度之母”,重视文化的解释,或文化的解释的解释或再解释。
作为研究技术和工具方法的田野工作,它强调通过观察与参与观察、访谈与深度访谈、谱系调查、自传调查、定点追踪和文物文献搜集等方法来获取研究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田野工作强调“文化互为主体性”,重视从主位和客位的双重视角去获取或分析同一则资料。
综上所述,田野工作不仅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是一种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研究技术及工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