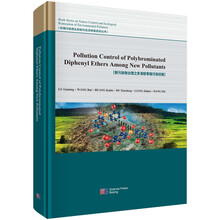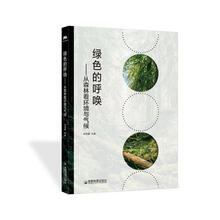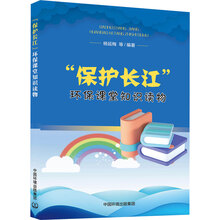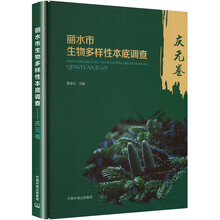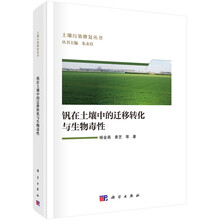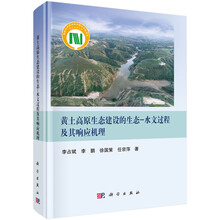第1章 生物质能发展现状与趋势
1.1 全球生物质能发展现状
生物质能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是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能源[《生物质术语》(GB/T30366—2024)]。人类对生物质能的利用历史非常悠久。传统利用方式是直接燃烧木材、废弃物和传统木炭等,这种利用方式持续伴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图1-1)。到2023年,全球传统生物质能利用量约为11111TW?h(约合13.6亿tce),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传统生物质能利用主要集中在建筑部门,很多国家居民的取暖、炊事仍然要依靠直接燃烧木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
图1-1 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构成
资料来源:Ritchie等(2023)
现代生物质能利用方式是指通过相对先进的技术对生物质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利用,包括利用农林剩余物资源来发电或规模化供热,以玉米、甘蔗和其他能源植物作为原料生产液体燃料,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进而提纯为生物天然气等。现代生物质能可以是固态、液态或气态燃料,在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都能找到具体的应用场景。根据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2022)的统计,2020年现代生物质能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约为5.6%,其中,工业部门供热的应用比例*高,约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2.7%,建筑部门供热为1.3%,交通部门为1.0%,电力部门为0.5%(图1-2)。
图1-2 2020年全球生物质能在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REN21(2022)
本图数据经过四舍五入,存在运算不等的情况
从具体部门来看,现代生物质能利用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供热领域和建筑部门供热领域,在两个领域的消费占比分别为10%和5.2%(图1-3)。工业部门的生物质
图1-3 2020年生物质能在各部门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REN21(2022)
能利用主要集中在造纸、食品加工和木制品等行业,所使用的生物质原料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生物质废弃物和剩余物。建筑部门的现代生物质能利用主要为区域供热。瑞典、德国、丹麦、芬兰和法国都是生物质区域供热的主要利用国。
全球交通部门消费的能源中约3.5%来自生物质能(主要是以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为代表的液体燃料)。2020年全球生物液体燃料的消费量为3.8EJ(约1520亿L)。生物液体燃料产量*大的国家是美国,约占全球总产量的36%(按热值),其次是巴西(26%)、印度尼西亚(7%)、德国(3.4%)和中国(3%)。全球生产的生物液体燃料中,61%(按热值)为燃料乙醇,33%为转酯化生物柴油,剩余为加氢生物柴油(hydrotreated vegetable oil,HVO)和少量先进生物燃料。燃料乙醇的原料以玉米和甘蔗为主,2020年产量约为1050亿L。美国和巴西两个国家的产量合计占全球总产量的83%。2020年全球生物柴油产量为468亿L,其产地分布比燃料乙醇要更具多样性。全球*大的生物柴油生产国是印度尼西亚,占全球比例为17%,其次是美国(14.4%)和巴西(13.7%)。
全球电力部门消费的燃料中约2%来自生物质。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在2020年达到约145GW。同期,生物质发电量为602TWh。2020年,全球生物质发电规模*大的国家是中国,其次是美国。
1.2 中国生物质能发展现状
我国生物质能利用形式多样,目前以生物质发电、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液体燃料和生物天然气为主。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2024)的统计,2023年我国生物质能开发利用量约8038万tce。其中,生物质发电利用量约5940万tce,占比73.9%;生物天然气利用量约46万tce,占比0.6%;生物质成型燃料约1300万tce,占比16.2%;生物液体燃料约752万tce,占比约9.4%。
我国生物质发电发展趋势良好,2023年,累计并网装机容量为4414万kW(图1-4),年发电量达1980亿kW?h。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为1688万kW,年发电量为550亿kW?h;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为2577万kW,年发电量为1394亿kW?h;沼气发电累计并网装机容量为149万kW,年发电量为36亿kW?h。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是近几年生物质发电的主要增长点,其装机容量在2017年已超过农林生物质发电(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2020)。
相比生物质发电,生物质非电利用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但近几年增长迅速。2023年底,全国生物天然气累计年产气规模为4.2亿m3,同比增长68%;生物质成型燃料年产量为2600万t,同比增长8.3%;燃料乙醇年产量为370万t,生物柴油年产量为280万t(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2024)。
图1-4 2015~2023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
资料来源: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2024),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2020)
尽管生物质能发展迅速,但是相比于我国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飞速增长,生物质能发展明显滞后。2007年我国曾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对2020年主要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设定了具体目标。回头去看,风电、太阳能2020年实际装机容量已是当时规划值的9.38倍和140.79倍,而在生物质能多项技术中,除生物质发电勉强达到当时的规划目标外,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距离当时规划目标相差较大,2020年利用量分别仅为当时规划值的40%、30%和50%(图1-5)。生物质能规模化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原料分散、收集困难,转化技术复杂、成本下降空间有限,以及终端利用缺乏激励、面临传统能源市场壁垒等,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图1-5 2020年可再生能源实际利用量与《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07年)中2020年规划量的比较
1.3 生物质能与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会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降水量变化、冰雪融化、物种迁移,以及热浪、干旱、洪水、气旋等极端事件的增加。长期气候变化将会增加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影响的可能性(IPCC,2014)。据估计,人类活动已导致全球变暖幅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约1.0℃,可能在0.8℃至1.2℃之间(IPCC,2018)。如果继续执行当前政策,世界将走在一条高排放的道路上,这可能导致全球气温在2100年升高5℃(中值估计),*坏情况下可能升高7℃(10%的可能性)(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 and China Expert Panel on ClimateChange,2018)。这样的温度将对人类和自然系统构成严重的直接和间接风险。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风险,201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提出了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的目标;同时还确立了2020年后国际气候治理新机制,以各缔约方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承诺为基础,以每五年一次的全球集体盘点为激励,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UN,2015;何建坤,2018)。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的评估,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或1.5℃以下的GHG排放水平与国家自主贡献所提出的GHG排放水平相差较大。截至2021年9月30日,占全球GHG排放一半以上的120个国家(121个缔约方,包括欧盟及其27个成员国)已经通报了新的或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按照新的或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计算,要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内,2030年全球年排放量必须在各国提交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方案基础上再减少13GtCO2-eq;若要实现控制在1.5℃内的目标,则须减少28GtCO2-eq(UNEP,2021)。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强调实现1.5℃升温控制目标的必要性。相比2℃,实现1.5℃升温控制目标可以明显降低气候风险,但同时也要求更为严格的减排进程,到2030年全球实现净人为CO2排放量在2010年水平上减少约45%,到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排放,因此迫切需要全球进一步强化减排行动。
生物质能是重要的碳减排措施。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发布的《全球能源行业2050净零排放路线图》(IEA,2021)中提到,在2050年净零排放情景下,2050年生物质能需要每年提供约100EJ的能量,其中60EJ来自农业和林业剩余物与废弃物,其余40EJ来自能源植物。2050年,生物质能将占全球能源总供应的20%,对全球交通、工业和建筑部门脱碳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世界主要区域和国家都将生物质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了《欧洲绿色新政》,提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计划在七个战略性领域开展行动,发展生物质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英国政府于2020年公布《绿色工业革命十点计划》,以期在2050年之前实现GHG“净零排放”。该计划中涉及生物质能的领域包括可持续航空燃料、住宅与公共建筑脱碳等。美国于2021年正式发布了《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公布了美国实现2050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节点与技术路径,其中特别提到生物质能是促进能源系统脱碳的关键组成部分。
发展生物质能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提到要“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合理利用生物质能”“在北方城镇加快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暖 因地制宜推进热泵、燃气、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清洁低碳供暖”等内容,这为生物质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物质能GHG减排特征形成了三点认识,可以归纳为零碳排放、全生命周期排放和负排放三个概念。本书尝试系统梳理生物质能的碳减排特征,并着重在后续章节介绍全生命周期排放和负排放两项。
(1)零碳排放。“零碳排放”是对生物质能碳减排特征的一个简化认识。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空气中的CO2,如果加工转化为生物质能,在其利用阶段会排放CO2。吸收和排放大致可以抵消,因而通常可对生物质能利用按照净零碳排放加以考虑(IPCC,2006)。
(2)全生命周期排放。随着生物质能在全球的规模化发展,很多学者注意到,在生物质资源获取和生物质能加工转换等环节可能会有化石能源消费,从而产生额外CO2排放,于是需要进一步对生物质能的全生命周期排放加以考虑。
(3)负排放。近年来,随着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各国加快推动碳中和目标进程,生物质能负排放潜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BECCS的生物能源可以将生物质能利用过程中排放的CO2进一步通过碳捕集与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技术封存到地质构造中,从大气中移除出去(Luderer et al.,2018;IEA,2013;IPCC,2014)。*新研究表明,需要大规模部署BECCS才能将全球的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和1.5℃之内(Clarke and Jiang,201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