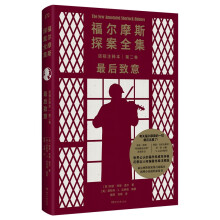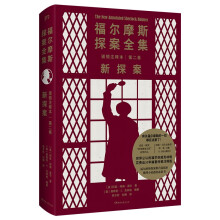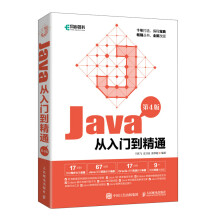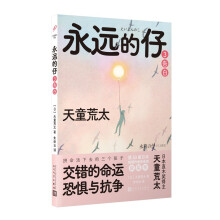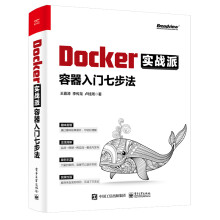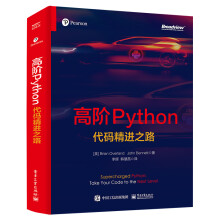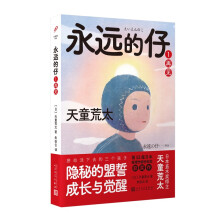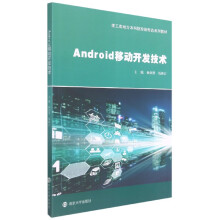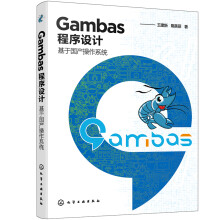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引言
深部岩体工程开挖施工已成为多个行业科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从水电站地下洞室群、深部矿山巷道、核废料地下处置库、地下军事洞库、深埋交通隧道,到干热岩、页岩油开采等工程,均涉及大规模的深部岩体开挖问题。例如,我国锦屏水电站*大埋深已达到2525m,我国*口超万米科深井——深地塔科1井在地下10910m胜利完钻。随着开挖深度的不断突破,深部岩体“三高一扰动”的特点更加显著,分区破裂化、摆型波、超低摩擦等现象更加明显,岩爆、冲击地压、突水突泥等动力地质灾害日趋频繁,人员与设备安全风险逐年递增。因此,亟须深入研究深部岩体特性与力学行为,揭示岩体灾害与失稳机理,为深部岩体工程安全控制提供理论支撑。
水电站深埋地下洞室群规模宏大,各洞室间空间布置紧凑,相互立体交错,且具有显著的“大跨度、高边墙、大埋深”特点,并同时面临节理裂隙发育和高地应力的地质赋存环境。而伴随水电站潜能源的大力开发,特大型水电站数量持续增加,各水电站洞室群设计埋深日渐增大,空间结构日趋复杂,单体规模日益提升。例如,我国近年来建成的白鹤滩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和乌东德水电站,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二、第四和第七位。其中,溪洛渡水电站地下厂房洞室群深部岩体开挖方量超过1700万m3;白鹤滩水电站地下洞室群深部岩体开挖量突破2500万m3,地下洞室群总长高达217km,主厂房跨度34m,长度438m;乌东德水电站左岸地下主厂房高89.8m。
水电站深埋地下洞室群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导致了爆破开挖施工风险和难度的不断攀升和爆破开挖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对开挖稳定性控制关键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在爆破开挖施工过程中,地下洞室群围岩稳定受到深部裂隙岩体力学特性、洞室断面形状以及洞室群空间布置等因素的影响,还面临爆破振动和瞬态卸荷等强动力扰动的直接威胁。因此,为保证当前特大型水电工程安全高效建设,必须全面开展岩体动静组合力学特性、洞室群爆破振动传播衰减规律、爆破安全精量化控制标准、岩体累积损伤与动力灾变特性、精量化爆破开挖施工工艺等科学技术研究,系统解决深埋地下洞室群爆破开挖施工围岩稳定性评估和控制关键技术难题。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 深部裂隙岩体不同应力路径下加卸载力学特性研究现状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基本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基础建设在向空间发展的同时,地下资源和空间的开发也在不断地走向深部,地下岩体工程的高应力特征也越来越显著。例如,锦屏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实测*大地应力为42~46MPa,*大埋深处地应力可达70MPa以上,*大外水压力为10.2MPa。岩石在试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力学特性与其所处的应力状态密切相关,加载与卸载是两种不同的应力状态,因此岩石在加载、卸载两种不同应力路径下的屈服条件、力学参数以及研究方法都是不同的。地下岩体工程的开挖,从力学本质来说,主要是卸载行为,岩体在卸载和加载条件下的力学性能有着本质的区别[1]。
研究者针对工程岩体面临的三向受力状态,考虑不同加卸载路径,展开了岩体的试验及理论研究。汪斌等[2]进行了常规三轴压缩试验和峰前、峰后卸围压试验,认为大理岩峰前卸围压试验的围压效应*明显,峰前、峰后卸围压黏聚力均降低,而内摩擦角均增加。黄润秋等[3]通过室内三轴卸载试验和破裂断口SEM细观扫描,研究高应力环境中不同卸载速率对大理岩的变形破裂及强度特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卸载速率和初始围压越大,岩石脆性及张性断裂特征越明显,卸载条件下岩体的黏聚力大大减小,而内摩擦角却稍微增大。李宏哲等[4]认为,大理岩体积变形几乎按照侧向变形的规律增大,峰前卸载条件下的黏聚力比加载条件下低14%,而内摩擦角比加载条件下高23%。刘豆豆等[5]的研究结果表明,峰前和峰后卸围压下的试样都表现出脆性破坏的特征,峰前卸围压条件下试样破坏更为强烈。高春玉等[6]根据升轴压、降围压的峰前卸围压试验,认为卸载导致黏聚力大幅度减小而内摩擦角略有增加。Li等[7]对具有水平层状和竖向层状的砂岩进行的加卸载试验表明,相比加载试验而言,卸载试验时水平层状砂岩的黏聚力增加而内摩擦角降低,而竖向层状砂岩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变化与水平层状刚好相反。张黎明等[8]对粉砂岩试样进行了常规三轴压缩后保持轴向变形不变的峰前、峰后卸围压试验,并对试样破坏特征、强度和变形特性进行了定性分析。黄润秋等[9]基于岩石试样的卸载试验,认为相对于加载试验,卸载岩石的黏聚力减小而内摩擦角增大。吕颖慧等[10]对取自大渡河大岗山水电站的花岗岩开展高应力下两种卸载方案的力学特性试验研究,认为岩石卸载过程中卸载方向的回弹变形强烈,扩容显著,脆性破坏特征明显,与常规三轴压缩试验相比,卸载时岩石的黏聚力减小而内摩擦角增大。刘建等[11]对采自重庆鱼嘴的砂岩开展保持轴压不变的峰前卸围压试验,从偏应力变化量角度证明卸载应力路径更容易引起砂岩试样的破坏,卸载条件下的黏聚力比加载条件下低1.2%,内摩擦角则高4.8%。从以上研究进展发现已有的卸载试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趋势:①对于初始固压效应的研究较多[2,3,5,7,8],而对于实时固压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②开展峰前卸固压试验的研究较多[2,4,6,9,11],而对峰后卸固压试验的研究相对较少;③对于试样变形特性的定性分析较多[2,3,5,11],而定量分析较少。因此,缺乏深部岩体的系统的峰前、峰后卸固压试验和相应强度变形特征及破裂机制研究。
此外,裂隙作为深部岩体力学特性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地下围岩及工程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含裂隙岩体的强度必然受到岩块和结构面强度及其组合方式的控制。一般情况下,如果岩体沿某一结构面滑动破坏,则岩体强度完全受该结构面强度的控制,称为岩体强度的结构面效应[12]。如果岩岩石面破坏,则岩体强度受岩块强度的控制。研究者针对裂隙的三个受力破坏特征及机制展开了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Nasseri等[13]和Niandou等[14]开展页岩的常规三轴压缩试验,分析了页岩层埋面倾角、固压与强度的关系,进一步探讨了层埋面倾角、固压、强度参数的影响,发现试样有三种不同的破坏形式,页岩层埋面倾角和固压是影响试样按不同形式破坏的主要因素。冒海军等[15]基于单弱面理论,研究发现随着结构面倾角的不同,板岩可以产生沿结构面滑移、剪切破坏及复合破坏三种破坏形式,固压增大会使破坏方式由复合破坏向剪切破坏转化。李宏哲等[16]对含天然节理的试样开展了三轴加卸载试验,研究发现节理试样的破坏模式包括穿切节理面破坏和沿节理面滑移两种。王在泉等[17]对含天然节理的灰岩进行加卸载试验研究,分析了试样破坏特征、强度和变形特性。向天兵等[18]通过其三轴压缩试验对单结构面岩石的破裂机制和强度特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当结构面为缓倾角时发生材料破坏(即试样自身破坏),当结构面为陡倾角时发生复合破坏,结构面倾角合适时则发生结构控制破坏,而结构面的存在劣化了岩石的力学性能,降低了岩石的强度和储能能力。李新平等[19]和肖桃李等[20]通过模型材料的加卸载试验,研究了含裂隙大理岩的强度变形特征及破裂机制。韩建新等[21]探讨了一次性贯穿裂隙岩体强度与裂隙面的倾角、黏聚力和内摩擦角及岩块的黏聚力和内摩擦角间的关系,得到了一次性贯穿裂隙岩体破坏形式的相关判据,用实例验证了裂隙角度与岩体强度及破裂方式的关系。
2. 深部地下洞室爆破振动效应研究现状
钻孔爆破法是深部地下洞室开挖常用的手段。爆破施工会对地下洞室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爆炸荷载作用下,爆炸应力波会使洞室围岩的力学性能劣化,从而影响围岩的稳定性。在地下工程中尤其是在水电工程建设中经常碰到大断面多工作面平行和交叉作业的格局,构筑物在重复爆炸荷载作用下,爆炸应力波会使导流洞群的岩体力学性能劣化,造成岩石强度和力学性能降低;或者使围岩内产生裂纹或使原有裂纹扩展,影响岩体的完整性,增加了支护和衬砌费用。特别是对于净距较小的洞室的爆破开挖,由于洞室间岩柱隔墙较薄,围岩压力大,爆破地震波传播到相邻洞室时洞壁容易发生剪切破坏或者拉伸破坏。研究者通过现场爆破振动测试对地下洞室的爆破振动效应展开了研究。
谭忠盛等[22]研究了复线隧道施工爆破对既有隧道的影响,采用有限元法分析爆破振动效应的原理及方法,并结合关寨隧道的施工爆破进行实例分析,得到了各振动参数时间历程。龚建伍等[23]结合小净距隧道现场工程实践,对小净距隧道中间岩柱在爆破荷载作用下的振动响应进行相关监测,分析振动波在不同级别围岩、不同监测位置的传播及分布规律。李利平等[24]结合庙坪分岔隧道工程实例,研究了其小间距段施工爆破的振动监测方法、爆破动力特性及其减振控制技术。Langefors等[25]通过研究提出以25cm/s的质点峰值振动速度作为偏于安全的边墙临界破坏标准,将60cm/s的质点峰值振动速度作为岩石形**裂缝的临界值。周同岭等[26]通过对正负高程差地形爆破地震效应的试验观测,得出正高程差地层效应增大、负高程差使之减小的结论。张涛等[27]对边坡爆破振动试验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地震波能量不仅随着高程的降低而减小,而且还受到边坡地形的影响,在变坡点处地震波发生绕射形**的震源,影响爆破地震强度。蒋楠等[28]、唐海等[29]和陈明等[30]通过理论推导和试验研究发现,当地形地貌变化较大时,高程放大效应较为明显。李新平等[31]结合现场试验数据与数值模拟,发现地下洞室建筑物对爆破振动具有放大效应。
此外,爆炸应力波不但对地下工程有直接的作用,当其在深部岩体中传播时,对工程围岩的稳定性也有重要的影响。在地下工程岩体爆破开挖过程中,围岩体所受的初始应力会发生改变,构成岩体的岩石及节理的力学性质都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岩体在动载作用下的响应发生变化,因此研究地应力(静载)对于应力波在节理岩体中的传播和衰减规律的影响机制,对地下工程爆破开挖及相应防护工程的设计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国内研究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超声波为工具,研究了不同轴压和固压作用下应力波在岩体中的传播规律。李造鼎等[32]对差应力状态(双轴压缩)下的砂岩和辉绿岩进行了室内声波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声波的衰减对试样物理性质的变化比波速更为敏感;在双轴压缩情况下,不同于单轴压缩或静水压情况,岩石的衰减系数随著主应力的增加而降低,当达到极限应力时,衰减系数急剧减小;侧向应力的增加,导致岩石的差应力发生变化,差应力越大,衰减作用越强。刘祖远等[33]研究了单轴压缩下声波在干燥和饱水的砂岩和大理岩中传播的速度和衰减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关于固压作用下应力波在完整岩石中的衰减机制,是应力波在岩石内部微裂纹表面及岩石晶粒边界摩擦耗散产生的。当固压较低时,岩石内部微裂纹闭合,驱使其产生滑动的摩擦力增加,而应力波作用下能发生滑动的微裂隙数量减少,因此应力波的衰减相应减小。随着固压的增加,岩石内部原有微裂纹发生扩展,新的微裂纹开始产生,应力波作用下能发生滑动的微裂隙数量增加,应力波的衰减也相应增加。
研究者基于霍普金森压杆对静载作用下较大幅值应力波在岩石(体)中的传播及衰减规律展开了研究。刘少虹等[34]基于改进的霍普金森压杆,通过分析不同静载下应力波的幅值、透反射系数等,研究了静载对应力波传播及能量耗散的影响机制。Feng等[35]研究了不同轴向静载条件下煤体试样中应力波的传播及衰减规律,定量分析了裂隙闭合和扩展两阶段煤体损伤演化对应力波传播及衰减的影响,并给出了不同阶段内煤体应力波传播与衰减的主导机制。理论与数值模拟方面,Fan等[36]结合位移不连续理论和特征线法,同时基于非线性模型,对地应力作用下一维应力波垂直入射单条节理的传播规律开展了研究,考虑了不同应力波幅值和频率的影响。范新等[37]通过数值手段对不同初始应力下应力波的传播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初始应力爆炸扰动及块体间的构造特征共同影响块体的运动,初始应力越大,径向应力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