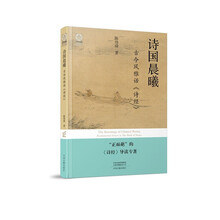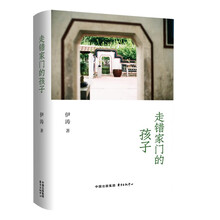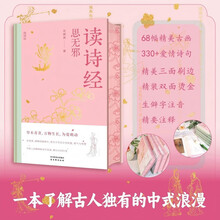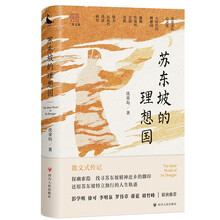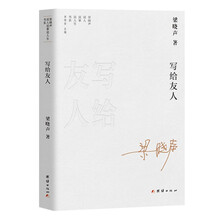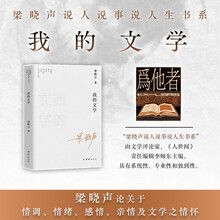我唯一的完整学历
一辈子干文化工作,常同文人学士打交道。当编辑有个习惯,遇见初识的文人学士,总要打听对方是在哪里出身的。因为一知道他毕业于某校某系,凭自己的经验,大概可以揣想出他的师承和学派,然后就有话好说了(同时也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了)。要是自己熟识这个大学的学术领袖,还给他出过书,效过力,接下去更大有吹嘘的了。
但是,这办法没法用在我自己身上。我除了小学,从来没在某个学校毕过业。说自己自幼失学,也对。可是,同龄人中,大概也没我上过的学校多。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为了向党“忠诚老实”,原原本本交代一遍自己上过的学校,当时记得已有十四五处之多。要是把小学、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大概有二十处吧!
前面说过,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除此之外,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想学一些技能,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上海人叫它们“野鸡学堂”)里瞎混,如是而已。不过就小学说,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现在更名为上海市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这得从头说起。
我六周岁时起初上的是上海普通的弄堂小学,那里全讲宁波话。我祖母是上海本地人,对这十分不满。在那里上学不到一年,就要我转学。她选择了附近最好的小学,在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现名康乐路)。凭我们的身份和家产,当然进不去。怎么办?幸好,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工部局做“大写”,即文员。于是我就冒充他的儿子,算是英国人驻沪行政机构“工部局”的职工子弟,优先免费入学。为了办这手续,我更名改姓。原名沈锦文,现在改名为王昌文,因为这亲戚姓王,他的孩子排行都是“昌X”。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为了进这小学,从此姓“王”。不仅此也,我还得同里弄里的一切小朋友绝交,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住在“棚户”,属“野蛮小鬼”之列,开口闭口要说“触……”。我记得,我平时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为进这学校,母亲连夜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西式衬衣,免得露出土气。
小学六年,平稳度过。在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办的学校读书,现在应当大力控诉其罪行。但我做不到。原因很简单,这学校名义上是工部局办的,可是主管人员却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大多是陈先生在南京办的一所师范学校来的)。这些老师特别的宽厚仁慈,谆谆教学。过不多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让我退学,反而同我商议恢复原姓——沈。从此,大概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我就叫“沈昌文”了(恢复原姓,名字就不恢复了)。
一九四二年底,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学校里不教英语了,改学日语。很意外的是,来的一位日本女老师,教学态度特别仁慈。当时日本士兵在上海十分凶狠,老百姓都非常痛恨。可是这位日本女士却同我们小学生打成一片,十分融洽。这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也因这缘故,我的日语学得十分努力,老师很称赞。 一九四三年中,小学要毕业了。小学校长章印丹先生很挂记我这个穷孩子。他专门把我找去,告诉我,要是我考得进也是工部局办的指定的中学,他可以为我张罗一笔奖学金。原来,当时上海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元老沈恩孚老先生八十寿辰,收了一笔寿仪,准备将之作为奖学金。我经章先生介绍,专门去见了沈恩孚先生的公子沈有乾先生。他通过审核,给我一笔资助,让我进了也是上海工部局办的著名的育才中学。可惜的是,这笔资助只够一年的学费。在育才中学上到初二,只上了一二个月,家里再也筹不出钱。于是,我只得悄悄地离开学校。所以要“悄悄地”,因为已经在那里白上了几个月学,怕学校追究。
这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店员工人,上海街头的所谓“小赤佬”,再也同学生生涯无缘了。当然,有时也冒充学生,同过去小学的同学闲混,但是自己知道,我只是个冒牌货而已。
六年小学生涯,十分短暂,但是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我从这里知道,只要自己肯向上,总会有人相助。以后尽管没上正规学校,可是说来不信,我的古文和英语,大多是一大清早在上海法国公园(现在叫复兴公园)免费学的。那里一位赵老师教《古文观止》,一位丁文彪老师教英语《泰西五十轶事》,都是公开的免费讲学。这大概是我所受的早期文科教育。每天在那里上完课,早上七八点,再赶紧去打工谋生。通过小学的经验,我深知,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是会支持年轻人学习向上的。P1-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