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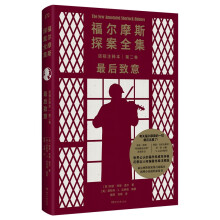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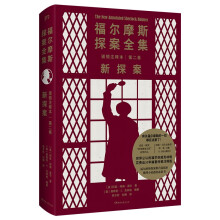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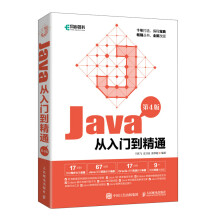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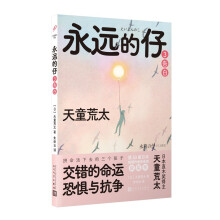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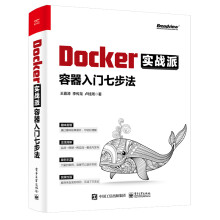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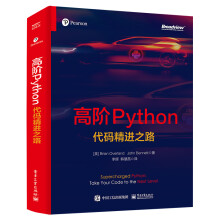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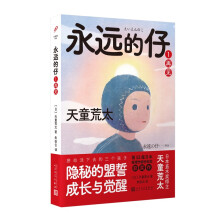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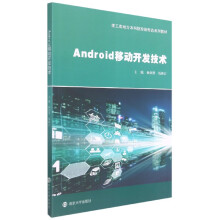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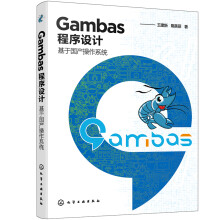
1.你知道一本书是“文学名著”,但你是否知道它何以成为名著?
“荒岛种田流”始祖何以成为名著?人变成虫的荒诞事何以成为名著?“三观不正”的出轨故事何以成为名著?
课堂让你知道哪些书是名著,本书让你理解它们为什么是名著!
2. 阅读不是竞速挑战,而是秘境探宝!
在这个知识焦虑的时代,阅读越来越像是竞速游戏和打卡挑战。当你被困在越来越长的“必读书单”中,是否忘记了文字背后的温度与惊喜?本书带你放下功利心,重拾探索的好奇,让阅读从“完成任务”变成一场私人冒险。
3.本书不提供标准答案,只交付寻宝罗盘!
“后现代”“解构主义”“复调叙事”“陌生化能指”……当学术黑话筑起认知壁垒,普通读者该如何接近文学?本书回归文本与情感,绕过术语与理论的迷宫,不设专业门槛,不作概念轰炸,为读者还原文学本来的魅力。
4.一本写给大众的文学启蒙读本+进阶指南
知乎文学话题优秀答主力作,从个体的阅读体验分享,到普适的阅读方法总结,
从文本细读方法论到作家经济史,从物象解码到时空哲学,十二个主题重塑你的文学认知。《堂吉诃德的眼镜》作者张秋子、《李商隐十五日谈》作者李让眉推荐!
5.在焦虑与困惑的时代重拾阅读的意义
当短视频蚕食专注力,当功利心主导选择,阅读仿佛已经成了无用的摆设。
但文学不是装饰品,而是凝结着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情感困境与生命智慧。那些被称为“名著”的故事,将是映照当下困惑的明镜。
你知道一本书是“文学名著”,但你是否知道它何以成为名著?
“荒岛种田流”始祖何以成为名著?
人变成虫的荒诞事何以成为名著?
“三观不正”的出轨故事何以成为名著?
……
本书针对大众读者阅读名著的常见问题,以深入浅出的讲解,帮助读者更新文学认知,构建起品读名著的阅读体系,从而真正领略文学名著的魅力,重拾阅读乐趣。
当你合上书时,那些曾被贴上“枯燥”“难懂”标签的经典,将成为你丈量文学世界的标尺。
第四章:跟作者掰手腕
了解成法,即帮助我们留意读和写之间,应当着意揣摩、反复练习的地方,从而提升我们阅读的收益。
文本细读是一种刻意的训练方式,其对审美能力的提升效果拔群。特别是对于信息密度较大的文本,文本细读能帮我们从忽略掉的细节里爬梳出许多关键内容。
面对经典作品时,读者的真实身份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侦探,是积极的参与者,是跟作者掰手腕的人。早一天适应这样的角色,就能早一天节省被浪费的大量时间,让书本中的知识更高效地为我所用。
我们以奥康纳的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里的一个段落为例,看看要如何适应文本细读的节奏和“侦探”这个全新身份。
医生告诉朱利安的妈妈,因为血压的缘故她必须减掉二十磅,所以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朱利安只好陪她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在Y处上一门减肥课。减肥课程是为年过五旬、体重在一百六十磅到两百磅的劳动妇女设计的。他妈妈在其中算苗条的,不过她说淑女不和别人谈年龄、体重。自从没有种族隔离以后,她晚上不再独自坐公交车,然而减肥课是她仅有的几个乐趣之一,对她的健康又十分必须,再说还免费,她说朱利安要是想想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至少是可以抽空接送她的。朱利安并不喜欢想她为他做的一切,不过每个礼拜三晚上他都会打起精神接送她。
首先,你不用考虑它讲了个什么故事,也不用挖掘所谓“背后藏着大量隐喻”,就仔细阅读每一句话,然后想想,自己能从这段话里哪些重要信息?
先静下来慢慢想。
读出然后咱们一句一句地拆解。
医生告诉朱利安的妈妈,因为血压的缘故她必须减掉二十磅,所以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朱利安只好陪她坐公交车去市中心,在Y处上一门减肥课。
这句话里出现了三个人物:医生,朱利安,朱利安的母亲。我们可以推断,朱利安的母亲是个超重的女性,而且超重已经影响到她的健康,使她处于高血压的困扰当中了。她生活中至少有一个部分是循规蹈矩的(每周三在Y处上减肥课),需要坐公交车过去。
有没有什么漏掉的重要信息呢?
仔细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位母亲不是以自己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作为“朱利安的母亲”出现,这就大不同了。“医生告诉老张”和“医生告诉小张的父亲”,虽然都是讲同一个人,但传达的情绪却完全不同。
继续往下读。
减肥课程是为年过五旬、体重在一百六十磅到两百磅的劳动妇女设计的。他妈妈在其中算苗条的,不过她说淑女不和别人谈年龄、体重。
作者没直接说母亲的情况,但通过介绍课程,我们也可以得出判断:朱利安的母亲体重在一百六十磅以上,年纪大约是刚过五旬。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甚至可以大概揣测出朱利安的年龄。再联系到前一句说周三晚上他要接送母亲到市中心,周三并不是休息日,那么朱利安的工作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对于接送母亲这个任务,他是欣然从之,还是比较反感?
这段话还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是“劳动妇女”,点出阶级属性。也许这一点,在朱利安的母亲眼中有些重要。再结合后面的“她说淑女不和别人谈年龄、体重”,在母亲眼里,自己是“淑女”,这是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至少在母亲眼里,他们是来自有教养的阶层,到这个“劳动妇女”减肥的场所活动,她可能多少有点自以为纡尊降贵,并希望和其他人保持距离感。
并且,她的“教养”里面,包括了“不和别人谈论年龄、体重这条,是不是会有一些可笑又令人同情的自私在里面呢?即是说,她是否希望,自己和别人,能够忽略她“年过五旬、体重超一百六十磅”这个事实,而认为她是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淑女”呢?
再往下读。
自从没有种族隔离以后,她晚上不再独自坐公交车。
“种族隔离”,说明了什么?也许聪明的你能够猜到,这个地方有比较浓厚的种族歧视氛围。那现在我们再补充一点前置知识:小说作者奥康纳,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美国南方作家。熟悉历史的读者知道,美国南方这个概念,也许会和“蓄奴”或“观念保守的白人”等词汇相关。具体到朱利安母亲这里,从这句话里似乎可以看出,她是很不赞成取消种族隔离的。也许这冲击了她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假想,也许这对她的三观构成了冒犯,也许这侵犯了她的既得利益。
然而她过去坐公交车,现在依然坐公交车。为了弥合教养、信念和生活的差距,为了保持某种优越感,当然你也尽可推测她是出于人身安全而把黑人统统假想为某类犯罪分子,总而言之,朱利安的母亲,做出了一种可笑的折中妥协:不再独自坐公交车。
我们继续。
然而减肥课是她仅有的几个乐趣之一,对她的健康又十分必须,再说还免费。
这一个递进,如果不是出于刻薄,就是在描述一种非常苍白的现实:朱利安母亲的生活是比较单调乏味的,以至于减肥课也是她仅有的几个乐趣之一。后面“对健康十分必须”和“再说还免费”,更是在暗示动机,好像对于这位母亲来说,不占这个便宜就有点吃亏一样。
她说朱利安要是想想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至少是可以抽空接送她的。
这句说明了什么?母亲也许曾为朱利安付出很多,也许没有,但她显然很在意自己的奉献,并希望儿子有所回报。并且——很有可能,这位母亲在生活里就经常通过亲情绑架的方式,令儿子就范。
朱利安并不喜欢想她为他做的一切,不过每个礼拜三晚上他都会打起精神接送她。
一种刻毒的幽默感。朱利安并不喜欢自己的母亲,他也许对生活也不怎么能提起兴致。对母亲的吩咐,他会照做,但并不是出于任何亲情的考量,而很可能是因为麻木,或者是为了堵住母亲的嘴。
大体来说,他不像母亲一样,那么在意“接送母亲”这件事情,
他只是遵命照做罢了。
好了,这只是针对一个非常简单的开头,所做的挂一漏万的分析。将以上侦探出来的线索汇聚起来,你会发现经典文本的叙事密度非常之大。
如果你掌握更丰富的知识,比如说人物原型、生活观念、叙述视角、美国南方的历史、种族矛盾等,就能在更广阔的讨论视角里还原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领略文本细读的乐趣,是阅读金圣叹点评的《西厢记》。
金圣叹是清代很有名的文论家。对这一位,大家熟知的典故,除了其点评、腰斩《水浒传》外,可能还有那句“花生米与豆腐同嚼有火腿滋味”的临终遗言。
实际上金圣叹不光点评了《水浒传》。他认为有六部书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并将其总称为“六才子书”。这六部书分别是:《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和《西厢记》。金圣叹发愿评批这六部书,以供后来者学习写文。可惜他中途遇害,只完成了《史记》《水浒传》《西厢记》的点评,《杜工部
集》点评了一部分,《庄子》和《离骚》则压根没来得及开始。
其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很出名。最早是唐朝的大诗人、和白居易并称“元白”的那位文学家元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唐传奇《会真记》,讲的就是这段故事。元代的王实甫把它改编成杂剧,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读《西厢记》对古人而言是很有乐趣的。除了作品本身质量过硬以外,因其笔涉情爱,有违礼教,成了禁书,反而更刺激。有句话叫大雪封门读禁书,很有意境。今天没有这些封建礼教了,我们不用像贾宝玉、林黛玉那样偷着看,更不用像薛宝钗那样看过了还假装没看过,不过紧张感也就没有了。今天各种爱情故事或情爱故事唾手可得,要是想看,大可去找小说电影,《西厢记》作为爱情故事从中脱颖而出,其实是蛮困难的。
就算要读诗词歌赋,杂剧也不是首选。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杂剧的文字还是很艰涩的。属于是那种,若是必读课业尚可完成,作为消遣读物却一定不想看的类型。哪怕是对戏剧作品感兴趣,也还有莎士比亚、易卜生,读起来也都比这个轻省多了,故事还更曲折。所以一开始我对《西厢记》几乎没有期待。
但金圣叹的这个评本,为什么又能打动我呢?
因为他的点评,帮我厘清了作者的每一个字词、每一段构设的用意、审美旨趣。通过他的点评,我很直观地看到了所谓作文的“成法”,即历代作者之间承袭的一些基本的写作规则,一些使行文跌宕好看的基本范式。
崔莺莺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主角。今天咱们看很多网文或者流行读物,主角一般都是开篇就登场,但《西厢记》不是。作者开篇先是借崔母之口,交代故事背景、前情缘由。随后崔母和女儿丫鬟下台,张生登场,接下来就完全是张生的个人秀了。书里交代他姓甚名谁,为何到此,并在寺里和尚法聪的带领下,赏玩寺院风景。
写莺莺的故事,张生先登场。金圣叹评说,这种创作布局是有缘由的,乃是一种有传承的笔法,唤作“烘云托月”:
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于云也;意不在于云者,意固在于月也。然而意必在于云焉,于云略失则重,或略失则轻,是云病也。云病,即月病也。于云轻重均停矣,或微不慎,渍少痕,如微尘焉,是云病也。 云病,即月病也。于云轻重均停,又无纤痕,渍如微尘,望之如有,揽之如无,即之如去,吹之如荡,斯云妙矣。云妙而明日观者沓至,咸曰:“良哉月与!”
想画月亮,月亮不可画,所以要画云。虽然画了云,用意却不在云这里,而是用云来烘托月。云画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月的呈现效果。你把云画得特别成功,观者都会赞叹:这月亮真好啊!
王实甫的故事要写莺莺。莺莺才貌性情,世上少有,金贵得很,也是观者最大的期待。但是你不能上来就写她,要先从别处下手,把观众胃口吊起来。这个“别处”,就是塑造张生的火候,张生就是莺莺的那块云彩。这人物火候不到,或过火,便是“云病,即月病也”。
你只有先把这个人物写好,张生立起来了,读者才会想,张生这么优秀,眼界那么高,他看见莺莺都目瞪口呆,那莺莺得是什么神仙?如此一来,大家闺秀才是真正的大家闺秀,难得的姻缘才是真正难得。
这个写法,就叫烘云托月。就像李安说,创作讲究“闷骚”。“闷”到火候,才能“骚”得起来。
张生匆匆一瞥见过莺莺后,辗转反侧,爱慕难舍。他想了个办法,既然不能直接见莺莺,就找莺莺的贴身侍女红娘去套磁,于是便引出了下面这段对话(加粗为金批):
(红出)(张生应揖云)小娘子拜揖!(红云)先生万福!(张生云)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红娘乎?(红云)我便是,何劳动问?(张生云)小生有句话,敢说吗?(红云)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有话,但说不妨!(张生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洛西人士,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千载奇文!(红云)谁问你来!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生年月日何用?千载奇文!(张生云)再问红娘,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出来便怎么?妙!先生是读书君子,道不得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凛若冰霜。即三尺童子,非奉呼唤,不改辄入中堂。先生绝无瓜葛,休得如此!早是妾前,可以容恕;若夫人知道,岂便干休!今后当问的便问,不当问的,休得胡问!(红娘下)
张生红娘这段对话,峰回路转,层层递进,写得属实精彩。
两人见面,一个拜揖,一个万福。
你是红娘吗?我是。
注意张生问话,你是莺莺小姐的侍妾红娘吗?招呼的是红娘,问的是小姐。其心切切,全在“莺莺”这里。
机敏如红娘,当时就明白七八分。她是怎么回的?这次就不是你问我答,一来一回了。红娘的反应是,把问题甩回去,创造主动权:我便是,何劳动问?是我啊没错,你问这个干什么?很有担当,还有点泼辣的意思。
这一下,倒是把张生给镇住了,他下一句便没了底气:小生有句话,敢说吗?我这里有一句话,想说,又不敢说。商商量量,心中有鬼。是你先主动搭讪,别人接了话茬,你倒是又要跟别人商量了。就用这八个字,张生刻画得跃然纸上。
红娘察觉到几分不对头,赶紧堵嘴,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你最好是想仔细喽。光这不算结束,堵完嘴,再补一刀:有话,但说不妨。我怕你来哉?
张生还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既见松口,既喜且慌,嘴一秃噜,开始报身份证号: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洛西人士,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金圣叹批:千载奇文!
这个“弹幕”,提醒那些没觉出好的读者,去把文字从头读过。说一句姓张名珙字君瑞,家住哪今年多大,怎么就“千载奇文”了?
陌生人报姓名籍贯,倒算正常;说自己今年多大了,也还能接受;哪天生日,多少有点怪怪的;至于交代婚姻状况,十足的怪胎!
不光红娘要奇,旁边人看着也是有点发癫了。什么时候要交代这些信息?说媒相亲的时候才需要呢!张生一瞥莺莺后起的心思,全在这一秃噜里爆发出来了。既不合时宜,又极端合适,亏他王实甫能想出来!
你张生不尴尬,那尴尬的就只能是红娘了。但红娘脑子更快,说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生年月日何用!
金圣叹批:千古奇文!
这一回,前面还没来得及觉出好的读者,怕是也要喷饭了。可不是吗,除了相亲,还有什么地方要生辰八字?那只能是卦摊儿上了。红娘故意指此言彼,揣着明白装糊涂,抢白对方,让张生自己回味,这是把他当个傻子涮着玩儿呢!
两个人物,语言风格完全不同,而且是互相衬着写,张生的呆萌和红娘的泼辣,相映成趣。王实甫一笔多用,两个人物全立起来了。
《西厢记》写张生、莺莺二人相见,也很有意思。莺莺是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原不应该有相见的机会。但如不相见,也就没有下文了。怎么既刻画出她的端庄,又使相见不显得突兀,这也是需要构思的。
王实甫并未写张生一开始便有意寻花问柳,或两人寺里见面就互 相搭话。他先写的是张生跟着和尚法聪,随喜游览寺中景色。这不是走过场的铺垫,而是张生专心游景,玩得很开心:
随喜了上方佛殿,又来到下方僧院。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洞房,登宝塔,将回廊绕遍。我数毕罗汉,参过菩萨,拜罢圣贤。
游兴尽酣,该各回各家了。看似文势已尽,偏偏曲曲折折,峰回路转,到这里,才引正题儿出来:“蓦然,见五百年风流业冤。”五百年的风流债,现在要开场。读者到达期望的谷底,开始放松之时,冷不防,正题儿到了。
对这种巧构,金圣叹告诉读者,并不是王实甫这个天才凭空想出来的妙手,这是承袭古人、有脉络可循的写作法:
凡用佛殿、僧院、厨房、法堂、钟楼、洞房、宝塔、回廊,无数字,都是虚字;又用罗汉、菩萨、圣贤无数字,又都是虚字。相其眼觑何处,手写何处,盖《左传》 每用此法。我于《左传》中说,子弟皆谓理之当然。今试看传奇亦必用此法,可见临文无法,便成狗嗥,而法莫备于《左传》。
前面写的那些,佛殿啊,僧院啊,法堂啊,应接不暇的,其实都只是笔端描摹的虚画。真正的用意,是落在作者眼觑的地方,也就是两人的邂逅。
作为读者,要看他笔端的描摹落到哪里,心里想的重心所在又是哪里。对有章法技巧的好作品来说,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步的,反而经常要用其不同步,构建起叙事的曲折。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使人初料不到,回看又顺理成章,恍然大悟。
金圣叹说,这是《左传》的写作法。自《左传》以降,作者们就已经开始这么写了。
后来我知道,金圣叹的说法也不是由他首创的,而是古代读书人的一种普遍认识。中国文学的大宗是史传文学,在文史未分家之前,叙述文字的“定法”,就已经出现。一件事情要如何讲,详略总分如何分布,由谁来讲,都有定法。
对此,章学诚有一段更深刻的认识: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
章学诚论述了由史到文的转变。古人把夏商周合称三代,三代经常是读书人寄寓美好理想的盛世。章学诚说,在三代以上,记录历史有固定成法,按照成法写成的文字,就是不具名的史料。三代以后,则是由史笔出众的具名人员,将这些史料勒定删成,而有撰述之私史。
成法保证了记录的取材范围、史学旨趣,是质胜文;有定名的撰述,把取材范围打破,且有更大的私人发挥空间。而前人的写法,会被承继下来,用以编排更广泛的素材。因此,就会出现文胜质的景象。章学诚立足于史,对这种不可扭转的现象持以悲观态度,说如此以来,史学“不亡而亡”。
但如果从文学立场出发看这个问题,则说明很多成法的东西被作文者吸收到自身的创作里,其取材范围乃至于文学的类型,也得到了解放。
文史分家后,“文”的这部分,自由跳脱,任意驰骋,在器局营构和具体的修辞上,又保留并优化着写作的法式,即构成金圣叹说的临文之法。举凡《三国》《水浒》,写法无不宗《史记》《左传》。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部优秀作品,是作者完全靠自己的脑洞才思完成的,其间有基本功,有前人留下的章法,有基本的写作理路。没有这些,单靠一股创意的灵气儿,也是难成佳作。
我们再看一下《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段落。上文的烘云托月以及《左传》笔法,在写这一段时其实都用到了,大家是否能辨别出来,能否觉察到曹雪芹是“眼觑何处,手写何处”呢?
刘姥姥由周瑞家的引路,到贾府打秋风。凤姐管事,事情自是在她那里了结。但刘姥姥并非上来就奔着王熙凤去的,她以为管事的是王夫人。等她费了好大力气进到贾府,也不是立时就认对了凤姐,而是先把平儿错认作王熙凤。
举凡周瑞家的、平儿、王夫人,岂非都是为写凤姐而描抹的托月之云?
文路行进至此,刘姥姥得到赏钱,原本即可告扰,回家过日子去了。曹公偏偏再荡开一笔,补写蓉哥过来借东西,随后贾母邀请刘姥姥逛园子,这才是主菜,并为之后的情节推进埋下伏笔。
如此曲曲折折,煞是好看,用的不也正是《左传》笔法?
有的小说,往往作者写到哪里,故事就推进到哪里,文本缺少蕴藉的脉络,让读者随波逐流,被动托管。要记住金圣叹的提醒:临文无法,便成狗嗥。
回过头看,如果当时我拿到的是简单点校过的《西厢记》原文,没有金圣叹在要紧处提点,牵动注意,使我留神看应当停目回味的地方,大部分阅读乐趣都会丧失,文章精华被轻易放过,也枉负了作者一片文心。
金圣叹将文本重新分卷,每一卷前都有一个总评,或归纳创作能力,或考镜笔法源流,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把握文脉,遇到相似的文本时举一反三,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也能运用起来。
花团锦簇的文字,背后是扎实的技巧,这些技巧的使用,是有普遍性的。小可以具体到字词上,大可以宏观到布局上。这种阅读练习,对品鉴和写作能力的提升,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后来的阅读过程中,当其他经典文本使用类似笔法,我也就能
第一时间发现,并比较优劣。
如《三国演义》写刘备访孔明。卧龙何许人,岂容你轻易碰上?不特刘备这样“欲伸大义于天下”的求贤者不能轻易碰上,对读者,罗贯中也需要吊足胃口,来一个匹配卧龙身份的精彩亮相。一访不到,二访不得,倒是把卧龙的交游圈子,影影绰绰勾勒出来,使人遥想,跟这些人交游的,得是何等人杰!自比管、乐,或许确实有真材
实料吧?
到第三次求访时,才“草堂春睡足”。诗写得非常自在,确实是隐居的卧龙。外面风云变幻,他这儿压根没时间概念,刘备三兄弟跑了三趟,这会儿都等焦了他也不管,睡到自然醒,才悠悠然起床了。这岂不也是烘云托月的手法吗?写卧龙的大才人间少有,就得写英雄刘备的殷勤备至。写月亮怎么美好,功夫都在云彩上。
不光如此,我还发现,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在处理安娜的登场时,也采用了类似于烘云托月的方法。
作为传主,安娜到第一部第十七个章节才出现。这一节写的是安娜的哥哥奥勃隆斯基去火车站接她,奥勃隆斯基接到安娜后,安娜才和读者见面。那么这本书前面十六章在写什么?
写的是“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
哥哥跟家庭女教师搞婚外情,嫂子发现了,跟他闹别扭。现在家里一整个失控状态。安娜作为救火队长——当然了,也是家庭美满生活幸福的典范——过来解决问题,劝解嫂嫂来了。
在多次精读这个故事后,我发现托翁这个开头的安排大有文章。看着是说故事,明线暗线里藏了不少东西。
比如说,托翁要写的安娜,是一个非常有活力、魅力四射的女人。这种魅力不光是貌美,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激情,周围的男人都很喜爱,而几乎是崇拜她。要把这种喜爱乃至崇拜的情感写出来,就要让读者也感同身受,被这个女人的魅力折服。
现在,托尔斯泰就面临了一个与王实甫相类似的问题:我要怎么写好这个女人,同时又不唐突这个女人?
托翁把笔先落到兄长家里,写兄长乱糟糟的婚姻状况。这便也是
烘云托月了。
《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第一句话非常出名,也非常经典:幸福的家庭大抵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相似了当然无话,各个不同,才能翻出花样,是入文学的好素材。
这句话不光由宏观到个案,顺利过渡到奥勃隆斯基的家庭矛盾中去,并且这个“幸福的相似”,也点了“安娜的家庭”一下。安娜的家庭算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福的?
那当然是幸福的,至少暂时是幸福的。她很漂亮,有热情,在社交圈里广受欢迎。她的丈夫身份高,对她好。她的孩子很可爱,她也很爱他们。地位、财富、尊严、亲情,要什么有什么。从经营家庭的角度讲,安娜是以成功人士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种成功,在她要解决的“兄长婚外情问题”的映衬下,尤其显得熠熠生辉。
烘云托月完毕,那幸福和不幸,有没有可能互相转化呢?
这或许是个问题。
序言
第一章 鲁滨逊的航船
第二章 始于荷马:故事的基本语法
第三章 搭建个人的文学史
第四章 跟作者掰手腕
第五章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日常”崩塌
第六章 作家们的钱袋子
第七章 “时间不存在了”
第八章 杰克船长的魔法罗盘
第九章 物象:帽子就是要戴在头上
第十章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第十一章 超越庸常
第十二章 照进现世生活
第十三章 通俗与经典
参考书籍
后记
这是一本悠游在中西文学之中的解读手册。在动辄套用宏大概念的时代,这样的写作显得轻盈与珍贵。没有说教与高蹈的姿态,凯鹅带着诚意走入文本深处,从文学的一句与一页中,掏出那些你以为早已翻过的细节,像从旧衣兜里摸出一颗糖,邀请你重新咂摸它的滋味,当读者惊喜地尝出了新滋味时,作者已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陪读。——张秋子,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堂吉诃德的眼镜》《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作者
文气发于脉理,心声辨乎辞情。本书藉由熟悉的文学场域为我们开启了一段新的阅读经历,读来如观计成造园,分花拂柳,完好地还原了“宛自天开”背后的“人作”匠心。——李让眉,诗人,作家,《李商隐十五日谈》《香尘灭》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