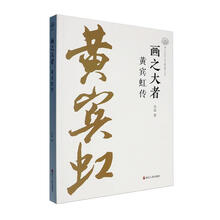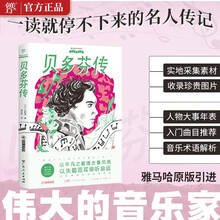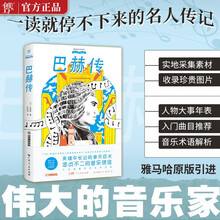《画之大者:黄宾虹传》:
黄宾虹初回故里,对这个房屋棋布、川流萦带,仿佛古画里江南平远山水的古朴村落却有着天生的亲切感,不久,对于潭渡的山阜、江流、溪湖、塘塌、道路、亭台、坊墓、宗祠、支祠、园圃、屋宇,他都能如数家珍了。村里有潭渡八景,其中丰乐溪南岸的滨虹亭在他看来是村中景致的最佳处。村口的函成台,左溪右冈,气势开阔,登上高台,视野开阔,远眺可将百里外的黄山天都、莲花等诸峰出没云海的奇秀胜景尽收眼底;近处则可见环村的凤山等山群峰竞秀,呈现平旷清幽的山水之美,这些景象无不令人欣然神往。直到后来迁回故土居住多年然后又离开潭渡,他才慢慢了解、清醒感知秀美风光下村落的破败落后、村民的保守愚弱。潭渡村自清嘉庆年间后已渐衰败,咸同年间遭遇战乱后更加衰落,富室多败落倾覆或迁徙异域,村中多不能安居乐业的游民。到了黄宾虹生活其中的19世纪末,由于乱世飘零和经济萧条,潭渡历史上曾有过的淳厚耕读礼教遗风、安逸民俗人情美德和黄家先人故庐一样慢慢凋敝衰微,文华兴盛的流金岁月早已不复存在,只存于前人的诗画中。黄宾虹后来在《潭上老屋》题画诗中说:“我族丰溪上,潭滨旧卜居。亭台留界画,卷轴散楹书。朴讷民风古,萧条兵燹余。敝庐原可葺,争奈迫饥驱。”黄氏家族世代居住在丰乐溪边的潭渡,向来民风淳朴,但经历战争后村落萧条凋零,到了黄宾虹回到潭渡又离开的年代,更是颓象呈现,许多老宅虽然可以修葺但无奈居住者多因饥寒外出谋生,所以只能渐渐破败,父辈称道的华丽亭台楼阁都消失了,只存在于画里,“楹书”有遗存的书之意,意思是世家大族所收藏的珍贵书画书籍也渐次散落或被卖,诗中道出多少无奈。黄宾虹日后对潭渡故里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带着那一代士人对乡土“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特殊情绪。但此时,这位少年对故乡亭台如画、藏书众多、民风淳朴的特质还是感到新奇喜爱的。
此次逗留潭渡期间,黄宾虹去过族祖修筑的课耕楼,这里已成族里教学所在地。所以当他来到楼里看到族祖惟贞公撰写的楹联“教子迟眠,数卷读残窗外月。呼童早起,一犁耕破陇头云”时,觉察这一联正暗藏“课耕”二字,也是历史上黄氏一族努力读书耕田、以里居为乐的生活形态的象征性概括,这两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黄宾虹在潭渡隐居多年后又离开家乡去往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但和成长于传统社会的同代士夫一样,课耕、山水幽居始终都是他心里的恒久理想,也因此成为他山水画的恒定题材,他不但画印象中的潭上风光和记忆里的课耕楼,后来还在很多画里借异地山水和虚构建筑来营造亦真亦幻的“潭上风光”和梦幻诗意的“课耕楼”。现实里他也曾在安徽池阳、北平陋巷、西湖栖霞岭筑造隐居之所来寄托“课耕”之思,读书、笔耕不辍。这都是家族文化毕生熏陶濡染的结果。
清光绪二年(1876),黄宾虹在潭渡读书、研读书画,待到岁末才回金华过年。清光绪三年春,他又奉父命与已到科举年龄的二弟懋庚等人再赴歙县应试,他参与府试,二弟应是参与县试。这一次没有父亲陪同,呼应黄定华当年离开家乡远行习商,隐约可见黄氏家族锻炼子弟的苦心。自此黄宾虹开始经常独自出行,探索陌生天地。
府试是童生试的第二场,由已考过县试的学子参加,试期多在四月。先前的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府试则由知府(直隶州知州)主持。学子通过府试之后才获得童生的身份,此后还要再通过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三年中的两次考试,包括岁试和科试)而且成绩合格才能顺利成为生员,不然仍是童生。成为童生也是很不容易的。府考需要连考三次。府考后黄宾虹和歙县西溪的汪福熙都文列高等,两个聪慧少年不免惺惺相惜,汪福熙就是他后来的业师、徽州大儒汪宗沂的长子,善于书法。后来汪福熙和弟弟汪律本都成为黄宾虹的好友,而黄宾虹又成为福熙长子、画家汪孔祁的启蒙老师,两家成为世交。
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咏村,号弢(韬)庐、韬庐处士。他少时好经世之学,曾入翁同龢门下,翁同稣认为他是命世之才,也就是顺应天命降世的人才,对他寄予厚望。太平天国起义时,他还曾被曾国藩聘为两江忠义局编纂,又被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聘为幕僚,后感觉不能舒展才华而辞归。清光绪六年(1880)进士。汪宗沂精研《礼经》,曾学汉学于扬州仪征刘文淇,学宋学于桐城方宗诚,汉宋兼通,著述颇丰,是徽派朴学后期重要学者,在徽学寂寥数十年后又将之重归朴学正流中,不愧江南大儒之誉。学生刘师培(刘文淇曾孙)为他撰了《汪仲伊先生传》,说他能秉承徽州同乡前贤婺源江永、休宁戴震的经学正统,推学于用方面能上法清初颜元、李塨颜李学派的实学,也与晚清泾县包世臣学说相似,评价得当。汪宗沂与近代浙江籍重要学人袁昶、俞樾等有交往。曾主讲安庆敬敷书院、芜湖中江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又曾居家设馆授徒,弟子有刘师培、许承尧、黄宾虹等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