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讲一个故事
“他喜欢把日常生活里的人摁到小说里。”《南方周末》记者宋宇说。“他”指的是阿乙。孙一圣直到拿到《骗子来到南方》样书,才得知自己被写进书里。“也不算是惊喜,就是惊吓。,’翻开书,他在第一章找到自己的名字,发现篇幅不大,内容无褒无贬,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下。
阿乙把一次聚会写成了短章《用进废退》。孙~圣来得晚,所以花在他身上的笔墨少。那天一早,阿乙的妻子的确收拾衣服去武汉出差,他和朋友也确实在咖啡店见面。戒烟后,生活变得空荡荡,阿乙开始喝咖啡。他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当黏腻的液体在喉咙里作怪,满脑子全是点错咖啡的沮丧,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书中,朋友拓跋晓春说的话真实存在,只不过他的名字和职务是编造的。现实和文学的交界地带,发生在走出咖啡馆的一刻:现实是两条鱼在玻璃缸里游;而在小说里,拓跋晓春和恋人在密闭的水箱里游泳,身体两侧是被割开的伤口。
《骗子来到南方》里有两篇挨着的寓言:《想学魔法的孩子》《追赶一只兔子》,主角都是一个不听大人话的小男孩,他们离家出走,但结局却截然相反——前者被孕妇推进热锅煮熟,剥皮拆骨吃下肚;而后者却意外撞破姑妈一家计划趁夜血洗自家的真相。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寓言用故事揭示道理。但从一开始,阿乙就没这个打算。他说:“我不是传递真理的人,因为真理不在我身上。我就是想让人得到一个故事。”
起书名时,阿乙和出版社达成一致:尽量轻快,容易引起读者注意。阿乙念了几个书名,《下面,我该千些什么》《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早上九点钟叫醒我》。他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富有动感,让读者快速获得一个清晰的认知。仅凭书名就可看出,《骗子来到南方》揭示了一桩事先张扬的欺诈案,将戏剧冲突推向高处,又戛然而止。
阿乙只写异常的人。《剩渣》是第二篇短章,书中铜浇铁铸、虎背熊腰的后生昭丂从县城来到北京,在酒吧与网友刚见第一面就迷失了自我。“从她开口说第一句话开始,我就像一条狗一样听从她了。”为了让爱人青春永驻,昭丂在抗衰机的运转下抽空了元气,最终成为一具干尸——听起来,像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聊斋故事。
第三篇短章《表妹》的聊斋色彩更浓。暮色中,肉塔一般的表妹出现在小镇杂货店门前,她吃空了杂货店,在第二天清晨变成了一条蠕虫。“没有眼睛、头颅和四肢,只有一节节隆起的肉。”孙一圣把“表妹”看成一个容器,阿乙写出了人内心深处难以启齿的羞耻感。
勇敢地拥抱新生活
“火车穿城而过,你能听到它鸣起的汽笛声。”阿乙上中学时,火车每天从学校附近经过,汽笛声一度让他忧伤。“就是你被远方抛弃了,被遗弃在原地。”那时还没有作家阿乙,他还是在江西瑞昌长大的小镇青年艾国柱。
即便在瑞昌生活了很多年,他仍然对每一个终将到来的冬季心生抗拒。南方的冬天冰冷彻骨,树枝是冷的,桥是冷的,枯草是冷的,水洼是冷的,他的双手皲裂、长着冻疮。阿乙在《骗子来到南方》写道:“我还记得一位养老院的老人不慎滚下床后,冻成冰柱。火化的时候,人们要用铁锨先把冰敲碎。”最难挨的不是寒冷,“父亲的脸和冬天一样冰冷,没有表情,只有简单的命令和无可挽回的裁决”。26岁的艾国柱想要离开,即便当时他有着一份父亲眼中的体面工作——警察,他还是决绝地辞职,家庭没能将他摁在原地。
当时,他身边有很多人为逃离做准备。有同事申请停薪留职,出去闯荡一两年,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更多的情形是,做足了逃离的准备,却迟迟没有离开。阿乙的结论是,当机会摆在眼前的那一刻,人内心生出的恐惧,致使人害怕拥抱新生活。他承认,他也害怕,自己是大专文凭,不会外语,从警校毕业,大致只能当保安。他说:“当你要出门的时候,想的都是对自己不利的地方,不会想自己拥有的东西。”
P5-7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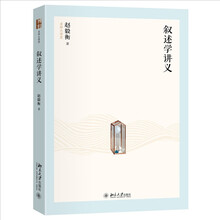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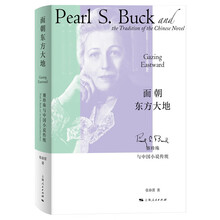
道,有深度。她关心的不是
某一部作品,而是我从过去
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史。她
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叙述
,对我回望过去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视角。
——刘心武
玉婷是一位优秀的记者
,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读者
。为了采访我,她做了充足
的准备,读了我很多作品,
读得很细、很透,并且提出
了一些新观点,这些观点让
我意外而新奇。她的文字优
美而透着真诚。
——周大新
我认识一些记者,他们
把新闻稿件视作高贵的作品
,精心织制。江玉婷就是他
们中优秀的一员。每次读她
的稿件都能感受到克制里夹
含着丰富、深邃、精妙。
——阿乙
和玉婷的交流很愉快,
我们聊了很多有关法医的现
状。《燃烧的蜂鸟》是我写
作十周年转型之作,对我意
义重大。玉婷的专访更像是
故事,带有独特的质地。
——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