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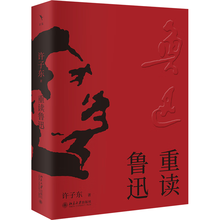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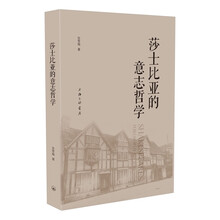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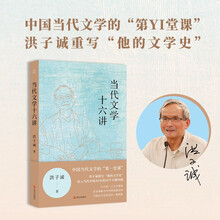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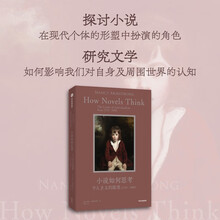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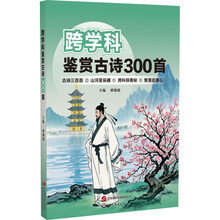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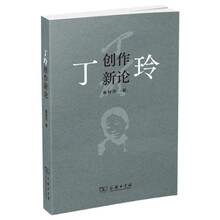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是“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一种。执行主编为常国武、钟陵、曹济平、刘乃昌。撰著人包括常国武、刘乃昌、钟陵、曹济平、周惠泉、王兆鹏、于北山等学界名流。该书对两宋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及各体文学演变进行了细致描绘和深入分析,材料丰富翔实,叙述准确充分,力图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作家、作品,从而全面地阐明宋代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第一章总论
第一节 宋代文学发展的背景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历来我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唐、宋两代文学最为辉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宋代不仅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王朝,其文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面貌。
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阶段,共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二百八十九年)、元(八十七年)、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也先后存在过辽、西夏、金及元等其他兄弟民族建立的若干政权。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这又是一个南北朝互相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宋代文学承先启后,又具有鲜明的独特风貌,无论就其总体成就还是各体文学的实绩而言,都足以与唐代文学后先辉映。后人言及我国文学,总是唐宋并称,诗、文、词皆是如此。宋代诗歌继承了唐诗的传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创造,出现了许多流派和优秀诗人,形成了与唐诗显著不同的特色,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争。宋代散文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创新,并以其显著的成就和重要的特色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词更是宋代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学样式,它渊源于唐五代,至两宋而发展成全盛的局面。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前代仅具雏形,到了宋代,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直接影响元代以迄明、清,因此后人又往往并称宋元话本、宋元戏曲。文学批评方面,不仅著述繁富,其内容和形式也都能扩大和深化前代的积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宋代文学的繁荣,是有着许多错综复杂、既带普遍性又具特殊性的背景和因素的。这些背景和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宋代文学经过逐步演进、变化等一系列曲折的历程,最终形成了一个颇有异于前代的总体风采。下面着重论述宋代几个带有自身特点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第一,宋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宋代开国之君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就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路,弹劾大臣,最后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路设有漕司、宪司、帅司、仓司四个机构,其中漕、宪、仓三司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至于对外政策,则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之收复燕、云的两次战役均告失败,故在宋初即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在经济方面,宋初便下令各州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悉辇送京师”,由皇帝直接掌握;又特设转运使管理各路财赋,务使“外州无留财”。另一方面,同前代许多封建王朝一样,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巩固政权,宋廷也采取了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改善工具、提高技术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让封建的租佃制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以提高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
采取上述方针政策的结果,一是军事上的孱弱,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以致慨叹国耻国难、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也就不断涌现出来,这是宋以前文学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二是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从而使得商品交换关系空前活跃,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许多大都市更加繁华,这些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有力地促进了歌词、话本、戏曲等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的兴盛发展。与此同时,为了防边而不得不大量增加军费(特别是冗兵的粮饷),为了绥靖甚至屈服于少数民族政权而被迫支出数以十万计的岁赐、岁币、岁贡,为了维持皇室的奢靡生活和官员的优厚俸禄又需要花费更可观的钱物,政府便千方百计地向广大劳动人民榨取钱物,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可谓“取财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条);加之准许土地自由买卖之后,不断的兼并和残酷的地租剥削,迫使农民不得不起而抗争,以致从宋代开国初期直到北宋灭亡,人民起义的烈火不断在燃烧,从局部地区蔓延到较大范围,从小股暴动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南宋时期,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因继续加重的赋税剥削集中落到了南方人民身上,起义仍然频繁而广泛。在这一背景下面,宋代文学作品中反映阶级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也就比前代更加丰富、深刻。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愈演愈烈,使得许多有识见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深感危机的严重,他们迫切要求改革,不仅见诸行动,而且奋笔为文,或与保守、反动的官僚进行斗争,或向集大权于一身的皇帝进献诤言,为求说理明晰,论证有力,文字风格就必须变艰涩险怪为平易畅达。两宋期间之所以出现众多气势充沛、说理透辟、文字流畅的政论散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宋代又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和优待知识分子、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建设的封建王朝。这是最高统治者始终执行“重文轻武”亦即“兴文教,抑武事”这一方针政策的又一必然结果。宋代初年,便非常注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一是大大增加制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并且以皇帝特恩的名义取士,由皇帝亲自召见考试合格的举人,甚至由皇帝亲临“殿试”录取士子。这些都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网罗、笼络人才的特殊措施。二是由政府兴办培养人才的学校,京师学校皆隶属于国子监,其名有十,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仁宗庆历四年(1044)以后,又下令地方大量兴办州学县学。受此影响和鼓励,私人讲学的书院也纷纷建立,著名的即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等,讲学者多为名儒硕学,所以也培养出不少人才。三是给予士大夫知识分子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俸禄。宋太祖曾立誓碑,内容之一就是誓不诛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两宋三百馀年间,历朝皇帝也确实极少直接下令处死过士大夫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取士,“名卿钜公,皆由此选”,从而使文人掌政成为宋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至于俸禄之厚,赏赐之多,前代也无法比拟,这在《宋史·职官志·奉禄制》中有着非常具体的记载,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确非夸大之辞。在文化事业建设方面,北宋初年便兴建崇文院收藏图书,仁宗庆历元年,王尧臣、欧阳修等人奉敕撰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收书凡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卷。靖康之变,内府藏书荡然无存。宋室南迁后,又极力访求图书,至孝宗淳熙间,成《中兴馆阁书目》二十卷,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宁宗嘉定年间,复成《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著录淳熙以后所得图书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影响所及,私人也开始著录图书,著名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代文化事业建设中尤足称道的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书以及《资治通鉴》的编纂,它们涉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其规模不仅远迈前代,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气氛中,各种类型的私人著述大量涌现;而由于印刷术的突飞猛进和出版商的应运而生,这些著述便更能得到广泛流传,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研习学业,创造了方便的条件。以上这些背景和因素,对宋代文学的繁荣影响极大。学而优能仕,仕而可以获得很高的俸禄,这就促使人们奋发读书,以求一第,知识分子的队伍便迅速庞大起来。因为俸禄甚丰,许多士大夫得以家蓄歌伎,享受声色之乐,于是最适宜反映他们流连光景、富贵绮靡生活的艳体歌词也因之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从总体上来看,更使宋代的知识分子在学识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过前代,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创造性地博采广收前人文学之所长,大量而熟练地运用古书中的成语典故,不管是叙事、抒情、议论,都能做到笔之所至,曲随人意,就是建筑在这一坚实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乃至陆游、辛弃疾等人,向以知识渊博而为人们极口称颂,而欧阳修这样的大作家当时却竟然有人讥讽他“不读书”,即此一端,已可见宋代知识分子腹笥之富和对知识的重视。还值得一提的是,历代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知识分子中似乎已有较大的变化。人有所长,交口称誉,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僚是这样(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对政见不合的朋友、同僚也是这样(如苏轼与王安石)。倘若文学主张不同,审美情趣各异,那也大都是通过文章来展开论辩,诉诸说理,极少人身攻击乃至大兴文字之狱(涉及政治的“乌台诗案”是极个别的例外)。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唐代知识分子间那种座主与门生的密切关系,到了宋代,已显然被文学集团、文人群体所替代,北宋的欧、苏、梅,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及江西诸子,南宋的四灵、江湖诗人词人群,乃至许多诗社、词社,都是在文学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成或十分紧密、或相对松散的群体,对文艺创作进行认真的交流、切磋和探讨。而在同一文学群体之中,也决不是强求一律,例如欧、苏、梅三人的诗风显然不同,江西诗派“三宗”的诗作也互有同异,苏门四学士对苏轼更不是亦步亦趋等等。宋代文学各个领域之所以出现众多的流派和风格,从而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从这里也不难窥见一些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