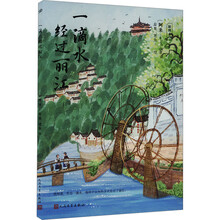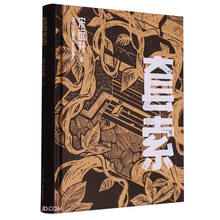熄灯
马建国到物业竞聘保安时,经理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问,看你的穿着,不像个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身体怎么样?保安的待遇并不高,可是对于身体不好的竞聘者,他们的条件比较苛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可不想找不必要的麻烦。
马建国踢着腿,抡起拳头,在自己的胸脯上擂了几下。意思说,棒棒哒。
学苑小区紧邻县一中,是个标准的学区房。精明的房主们,买了房并不住,而是租出去,得到一笔不菲的租金。
马建国负责小区的晚班,值一夜休息一天。有时,马建国白天也来转一转,东瞅瞅西瞧瞧,一副对什么都不放心的样子。同事们乐于他这样,毕竟省去他们不少的事。
孩子们放学晚,晚上十一点开始,才陆续从教室里回来。这时候的马建国,一个一个地看,生怕哪个孩子没回来。
等孩子们全部回来了,他才在值班室里喝口茶、吸支烟,之后到院子里溜达溜达。
窗户亮着灯,各家各户好像比赛似的。
马建国心头浮出隐隐的痛。孩子们真不容易,压力山大啊。
一般到深夜十二点钟,窗户里亮着的灯,才陆续熄灭。也有个别的,跟黑夜较着劲。
二单元四一五就是个别的,灯亮到凌晨的情况时有发生。
马建国的两张眼皮打着架,一个说,困,睡吧;另一个说,睡吧,困。而看着四一五的灯光,马建国睡不着。马建国想打个电话说一声,太晚了,熬坏了身体,不值得。电话拿起来,又放下。或者,号码拨了一半,又把电话挂掉了。
四一五住着祖孙两个人。孙女上学,奶奶陪着。像这样的家庭在县城很多,爸爸妈妈到外地打工,留个老年人守着。
孩子叫王小妮,读高二,正是冲刺的阶段。奶奶常年吃中药,一缕缕熬出的中药味,通过门窗的缝隙钻出来,在院子里游走。
王小妮背着沉沉的书包,从门岗走过。孩子的成绩怎么样?马建国倒不十分关心,他关心孩子的身体。孩子的精神不错,走起路来蛮有劲的,马建国笑了笑,觉得那天的空气真好,或者天气真好。若是孩子的精神不好,走路蔫蔫的,跟霜打了似的,马建国的心,也像孩子的书包一样沉沉的。
有一天,孩子从门岗经过,马建国悄悄靠上去,打了招呼,孩子,上学去?其实,马建国的问题是多余的,他知道孩子是上学去。孩子愣了愣,停下脚步,盯了马建国三秒钟,点了点头。马建国张了张嘴,还想问什么,孩子低下头,悄悄走开了。
……
回响
老沙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
下班了,老沙还穿着一身税服在家里晃荡。老伴撇了撇嘴说,老沙,咱想开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谁没有这一天?
老沙不接老伴的茬。心想,三十多年啊,一眨眼的工夫。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大声对老伴说,我那一套春秋装干洗了吗?
老伴似乎没好气,嘟囔着回答,洗了洗了,干吗非要干洗?浪费钱!老伴看了一眼老沙脖子上的那条脏兮兮的领带,再嘟囔着说,你脖子上那条链子,也该洗了。
老伴不叫领带,叫链子。反而把老沙逗乐了。
办公室里,老沙在看报纸,敲门进来一个人。您是沙局长吗?
老沙想,沙局长是谁?谁是沙局长?老沙瞅了瞅办公室,就自己一个人。再瞅瞅来人,一个高挑的女士,笑容可掬地冲着自己微笑着。老沙问:你是?
女士把一个纸袋放在茶几上,回答说,我叫于子英。
于子英?老沙开动脑筋,却想不起于子英是谁?
于子英坐下来,眼圈开始发红,继而抽泣起来。
老沙慌了。姑娘,您这是干什么?
于子英不回答老沙的问话,擦了一把泪,反问了一句,您老还记得于屠户吗?
三十年前,老沙还是小沙,刚到大别山区一个三面环山的偏僻小镇工作。穿着一身蔚蓝的税务制服,小沙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第一次上街收税,就碰到蛮不讲理的于屠户。于屠户一脸横肉,手里的刀子明晃晃的,不时在一个铁钎子上当当。于屠户眼睛里露出凶光,说老子从来没缴过税!
小沙想,从来没缴过税?好大胆,这不是明摆着的偷税漏税吗?凭着一腔热血,小沙坚决不答应。
一来二往,急了眼的于屠户,挥舞起了刀子。
小沙受了伤。于屠户被抓了起来,关进了拘留所。
没想到,于屠户血压高,在号里抢救不及时,死了。
每每想起这件事,老沙心里都隐隐作痛。在于屠户的葬礼上,一个小姑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把老沙的心都撕碎了。
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把他调到了另一个税务所。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里,自己由小沙变成了老沙。每年,他都向于家寄一笔钱。他想,家里没有了顶梁柱,日子怎么过呢?但是在落款上,他从不具名。
于子英说,我就是于屠户的女儿。
老沙站了起来,警惕地盯着于子英。
……
画桃
文件很快下来了,马之途任河湾村扶贫队长。组织部迅速作出安排,于两日内报到上岗。
河湾村位于鸡鸣听三县的地方,一条60年代人工打造的茨淮新河,在这里调皮地拐了一个弯,便一路东去,入淮河,进洪泽湖。
马之途想,河湾村可能因此而得名吧。之前,马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