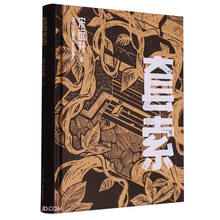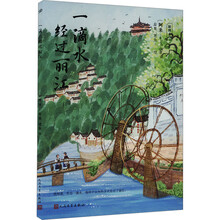荠雨花
二三月软人。
二三月春风和煦,春光轻柔柔落进邻家院门。
日光迎夕晒,门做两用,大门不消过多介绍,长长的高门槛打出世之日起便自我标注,用来走人的。
唯有男人的长脚板才撑得起如此宽高。
垛,陆石桥方言中门垛的意思,芦叶最爱做的事便是发呆,目光伴随夕晒的光照,自然而然转移到门垛上。
门垛,一面半开的小门栏。
不知怎的,上到小学的芦叶总能想起课本中晏子使楚的情节,书里的门垛,该比邻家大。
该比邻家大,芦叶背着家里人多次去邻家看过陆石桥畔独此一户的小门垛。
小孩儿联想力没边没沿,发散开来如陆石桥畔忽而远行的船家,网到鱼吃鱼,无鱼就着月光温壶烧酒般自在。
自在如春画婆婆家,也不由得门垛边上堆满荠菜花。
有讲究,你小孩家不会懂,爸妈敲打起芦叶后脑勺。
二三月软人,代代相传的老话,寓指进入二三月后,春风拂面的畅快感,一扫冬日寂寥寒冷,与之而来的便是四时之中最温和的日光。
流年似水,日光洒落河面,映在人身上,披了件袄子似的,一个字,暖。
暖,也恼人,独属于春天的烦恼。
春暖,花便会开,陆石桥畔最先绽放的花儿是哪一朵,大伙抠后脑勺也说不上一二,谁家花最香,通常一闻便知。
许是沾了名字里同样带着春字的福气,春画婆婆侍弄的后院里,总有四时长香溢出。
且经久不息。
飘于河面皆可闻,时常凭借花香就能判断春画婆婆的所在,陆石桥畔的养花人里,婆婆家种类算不上多。
其胜于精,精致的精。
这点上,芦叶具有十足发言权,河道破冰解冻的时日里,一簇簇待放的花骨朵藏于苞间,像小女孩害羞的脸,红扑扑,与让人观后生厌的大红色无关,若仔细观赏过春画婆婆后院中含苞欲放的各式花朵,便能明白略施粉黛的形容,并非戏言。
放晴的早春天,晨雾未散,晨气被云里的日光映射,落在花间的露水,跟洗过脸的小女孩别无两样。
四时常相往,迎夕而来的春光打在陆石桥墩上,连半开的花朵都软绵绵地想缩回身躯,更别提六畜。
……
酒钱榆
榆钱粥,好吃不腻味,多少年前,说来算去也没有多久年月。
飘落檐前的榆钱叶片,由青翠转为古铜木色,藏于屋瓦间。
不过十根指头缝儿流走的日子,年,月,日,三位一体经久不息,陆石河水般川流,复又归于平静。
只留下生茧的指头,朝阳洒落,年月走过的痕迹清晰可辨,日子叫日子日复一日打磨老旧,步履渐而蹒跚。
榆钱叶,能入酒席,青葱招展的叶片,较之同季其他树木,多有两分娇羞,叶片招展却绝不尽数展开,中心处凸起小核让自然蜷缩的叶脉呈小范围包裹。
活似油锅里走过一遭的扇馍。
扇馍,陆石桥茶余饭后上佳的吃食,佐以饭食能撑起一顿可口佳肴,烧起小半锅热油,翠云婶做来,得心且应手。
翠云婶,陆石桥畔的活钟表,一生一辈的后生喊她婶,再往下辈儿的唤作婆,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年纪,常人眼里,翠云婶自带两三分不常见的英气。
换句话讲,比常人多了份果敢。
任榆钱树压过屋瓦也不修剪,便为最好佐证。
压就压,给它压过顶都好看,翠生。
榆钱发于春,早春的寒气将河水解冻,惊蛰过后,万物于时令中,泥土里钻出,蛰伏过一个冬季的和煦暖风吹过陆石桥畔的人家,吹绿树木枝叶。
榆树,亦从黑白的单调色彩中走出,一袭水墨叫季节添上色彩。
碧莹莹,映在老城人眼中,却只剩下单调的绿色。
单调?
葱茏着咧。翠云婶不比其他女子,喜欢花朵,她说乱花渐欲迷人眼,她说浅草才能没马蹄,葱茏的榆树枝杈,抽发出嫩绿色苞子,不消几日光景。
再抬头时,一簇簇翠盈满枝。
长势喜人亦诱人,挂满枝头的榆钱叶片,随春风舞动,少女腰肢般轻柔,好的榆钱叶必然晶莹饱满,逃不开翠生二字。
翠生,陆石桥方言,寓意翠绿春意的生发。
能吃吗?
孩子们对于鲜嫩招展的花叶,往往报以生津的口舌,躲不开老辈人一顿温和的敲打。
榆木疙瘩!
净晓得吃,也不开窍,弄熟才能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