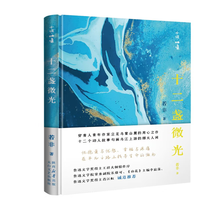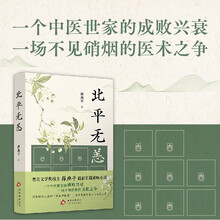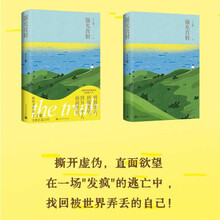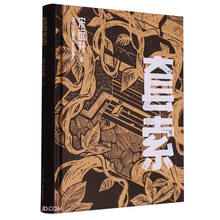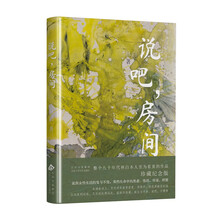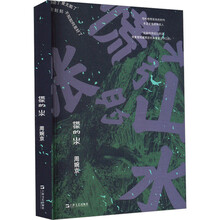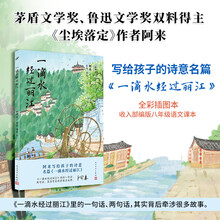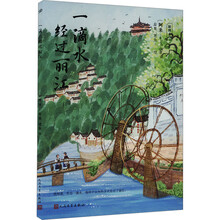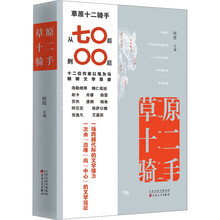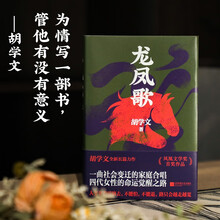这是一组村庄的年画;
这是一段村庄的秘史。
一曲曲秦腔、一声声乡音,在我的耳际反复回荡。这是我读了即将出版的散文集《风从故乡来》后之感觉。
作者倪红艳,是我们董坊塬上的女才子。我早年的记忆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印象较深处,有一年春节村里耍地台社火,她扮演扑灯蛾,很显灵巧与可爱。后来,这只扑灯蛾竟然扑进了西北大学;再后来,她又变成孔雀向西南飞了。以前,由于多种原因,我与作者未曾交际,只知道她很优秀,有鸿鹄之志。
在作者笔下,故乡那些熟悉的人物、景物、事物是那么亲切,甚至连每一块泥土、每一丝空气、每一声蝉鸣都是那么温暖。作者童年时虽随父辈们受了不少委屈,流了不少泪水,但在她的笔下,对故乡的情感并不是怨,而是无限的爱。
高尔基说:文学即入学。散文可以写人,可以写事,也可以写物。但塑造人物形象,仍是散文创作的重中之重。
在《父亲送我上大学》中,作者没有过多地描写父亲的外形,而是描述父亲的情绪变化。父亲在大学里办手续时情绪兴奋;办完手续后情绪低落;“要我注意这注意那”;然后他哭了;然后“他一步三回头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作者用情绪变化塑造人物,与朱自清的《背影》有异曲同工之妙。
《丁家山》中那个小男孩,作者是用行为塑造人物。小男孩似乎连名字都没有,作者只用他的几个行为,一点“鼻涕”,就将一个纯朴、可爱的小男孩刻画得淋漓尽致。《爸婆》中,上炕不脱鞋的爸婆;《木匠》中,担箱子串乡的木匠;《老先生》中,写春联的老先生等人物形象,作者均刻画得形神兼备。
语言是一个作家水准的试金石。“村庄物事”的语言朴实而有质感,厚重而有灵气,既耐读,又耐品。
诗意化的语言:
“腊八,拉开了年的序幕。”(《腊八粥》)
“灯笼,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它一直照着家乡的村庄。”(《灯笼年年红》)
有画面感的语言:
“一把镰刀、一顶草帽,外加一袋炒面,应该是他们全部的家当。”(《麦客》)
“马家湾就是从大路上朝旁边的坡下弯,一弯连一弯,不知弯了几弯,就弯到了山庄的院子。”(《山之脉动》)
哲理化的句子:
“我想,他的眼神一定穿越了这炎热的夏,想起了麦子的前生。”(《麦香的味道》)
“马家湾很小,小得只有两户人家;马家湾很大,大得养活了一个生产队的人马。”(《山之脉动》)
作者这样的语言,不胜枚举。
作者的散文还有一个更主要的特色,就是以细节取胜。
《社火》中有一段细节描写,表现文先生和海先生给扮演社火角儿的孩子们画脸的过程,细致入微。作者给先生们画脸过程,一连用了沾、扑、坐、叉、板、托、描、站、瞧、画等十个动词,将先生们的神态刻画得细腻而生动。被画脸的孩子只描述“仰着脸一动不动”,主次分明。孙犁先生曾评价贾平凹的早期散文是“细而不腻”,我认为作者也是。
作者的散文以风轻云淡的心态,娓娓道来。看似不太重视结构,其实并非,只是不露痕迹罢了。这里以我偏爱的《进城》为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