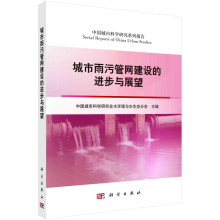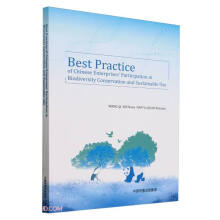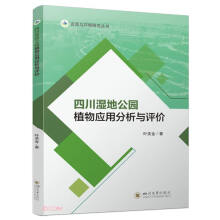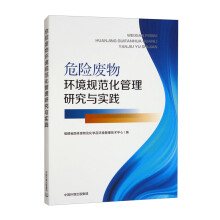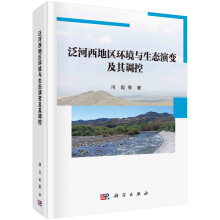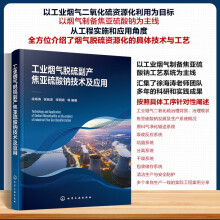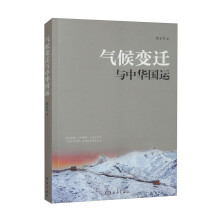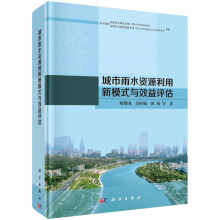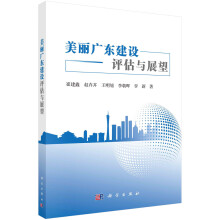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 世纪末,由国际科学理事会发起的“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 强调了城市化发展中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间相互作用对全球范围内环境变化影响的重要性[1]。在该计划的推动下,城市化带来的全球各个尺度上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及其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2,3]。其中以全球范围流域内水文过程变异、水质恶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自然河湖生态功能逐渐丧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尤为严峻[4,5],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学科研究开始围绕人类活动影响下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流域内生态格局的破碎化[6,7]、自然水文过程的改变[8,9]、水环境的恶化以及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等问题展开[10-12]。学者力求通过对上述变化趋势与作用机理的分析,提出解决突出的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策略,*大限度地恢复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然而,由于流域性问题的复杂性与所涉及学科的综合性特点,现有的研究尚未针对流域自身多元化的属性,形成一套综合其内水文、水环境与生态多个要素的方法体系[4]。与此同时,现阶段对流域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举措多从宏观的规划层面或剥离流域内各个要素的更加微观的机理分析层面展开[13,14],无法满足流域系统性规划的需求,也无法建立起流域生态系统内各个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基于此,从流域自身结构、功能与关联要素的分析入手,探讨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尺度,流域景观格局特征的变化及其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解决现有的流域性问题与提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规划建议尤为关键。
流域作为水文循环的基本单元,是自然、社会、经济共同作用的复合生态系统,需要从系统多元化的角度展开人类活动对流域内生态环境作用的研究[15]。吴刚和蔡庆华[16] 提出了流域生态学的理念,研究流域内不同景观和不同生态系统间信息、能量、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并强调流域内景观系统结构层次的丰富性与组成要素多样化的特点。该理论认为流域内自然生态要素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系统内各个层次发挥作用且影响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不仅涉及了宏观流域尺度、中微观河流廊道以及局部河段尺度,还囊括了河湖水系、山林田园、城市建筑群、生物与人类等自然与社会的多种要素[17]。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从系统多元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的流域内各个尺度景观格局特征的变化及各要素的响应奠定了理论基础与跨学科交叉探索的方向。回顾过去20 多年间该研究方向的已有成果发现,由于学科间跨度较大的现实阻碍,研究内容均分散在自然地理学、水文水利学、景观生态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侧重点均不同且各自纵向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多维度、多要素的跨学科系统综合研究已成各学科领域讨论的焦点[18,19]。在国家政治层面,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新要求,也再一次强调了统筹考虑各自然生态要素的重要性,并突出了跨学科系统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与时代意义。
综上所述,本书以广州市北部受城市化迅猛扩张剧烈影响的流溪河流域为研究区,开展剧烈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生态水文效应研究。流溪河流域是广州市重要的水源地之一,供给全广州地区近60% 的饮用水[20]。所在辖区已在2015 年前被逐步纳入广州市辖区规划范畴,这是推动流域内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剧烈变化的直接原因[21]。流域内部分自然用地被建设用地侵占,河湖水系、自然山林等原生生境被逐步人工化,原本的山、水、林、田、草景观格局遭到破坏,水环境条件逐步恶化,水源功能也逐步地丧失[22]。与此同时,流域范围内大量物种因栖息地的改变逐渐减少,物种多样性也不断降低[23,24]。这意味着流溪河流域现阶段正面临着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矛盾的现实困境,迫切需要明确人类活动对流域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改造带来的现状生态环境问题的作用机理,以此为基础提出协调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流域规划与管理策略。上述问题在流溪河流域开展的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其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带来的水文过程变异、流域内污染物浓度分布的差异[25,26],评估了流域内水环境条件与水生物健康水平等[27,28]。目前,尚缺乏分析流溪河流域多尺度景观格局特征变化及其带来包括水文、水质与生物条件多要素响应变化的研究。
综上,本书基于流域生态学理论中系统综合的分析视角,从多尺度出发开展人类活动影响下流溪河流域内景观、水文、生态多要素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机理研究,以期构建一套多因子耦合分析多尺度、多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流域多尺度景观格局特征演变及其生态水文响应的研究方法,丰富流域生态水文学理论,为流域景观可持续规划与生态保护提供参考。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1.2.1 流域景观格局演变研究进展
1.2.1.1 流域景观的定义
国际上目前还没有流域景观概念描述的统一标准,然而对“流域”与“景观”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研究与论述却发展已久。流域是一个基于自然水文过程发生的地貌水文系统单元,囊括了该单元内各级河流及其所在的汇水区域,承载了山、水、林、田、湖、草、生物、建筑物等多种自然与人为要素,也是人类生存与活动开展的关键区域[29]。景观的概念则更为复杂,从德国地理学家提出的描述某个地理区域总体特征的概念出发,逐渐发展到涉及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并扩展与丰富成为一个描述人为与自然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结果的整体性、综合性、可视性与实体性兼具的概念[30]。它可以是特定的自然或文化的地域符号,可以是单一或系统的斑块型的空间单元,也可以是自然环境与人为要素的组成部分,如树木、水体、草地或住宅等,或是某一类具体的自然或人为要素的整体表征和格局,如植被景观格局、城市景观格局等,甚至可以是整个地球的面貌、一幅风景图画、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等。这两个概念均强调了其融合自然与人为各要素的系统性特征以及多学科领域交叉的综合性特征,重视自然与人为要素在一定地理空间单元下的相互作用,并囊括了多个尺度与多个要素,具有丰富的地理、生态与社会意义。景观与流域两者的概念均较为复杂,但流域的概念限定了描述景观的实体空间范围,景观的概念则聚焦了描述对象—在流域空间单元内自然与人为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流域景观的概念是指基于对流域这一空间尺度范围内的多尺度、多要素相互作用的景观客体的描述。
目前,与流域景观相关的研究中*常探讨的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的流域景观格局变化特征的分析,即将流域景观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范围内各自然与人为景观类型的占比变化和空间组合特征,强调其景观格局整体性特征生态意义的时空变化[15]。在该理论下开展的流域景观研究多聚焦于宏观流域尺度,涉及流域以下尺度景观特征变化的研究成果较少。在20 世纪末到21 世纪初,Ward[31]提出河流景观概念,并强调将河流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以水文地貌为依托,分析生物与环境要素在河流四维时空(纵向、横向、垂向、时间向)中的相互作用。该四维时空结构不是孤立于流域而单独存在的,而是在其自身所在流域结构框架内的,它描述了围绕着河流本身所在河道及其周围的泛滥平原,从上游至下游、地表至地下、静态至动态的河流群落生境与环境梯度的动态变化特征。国内学者吴刚与蔡庆华[16]提出的综合了淡水生态学、系统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域生态学理论也强调了流域的多层次结构特性,认为流域是包含了高地、滨岸带与水体的水陆综合体,从宏观到微观可划分为五级(图1-1),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与干支流的结构体系。
图1-1 流域生态系统的五级结构体系[16]
这两个基本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立足点虽然不同,但却互为补充,均强调对流域的系统性研究。这为本书探讨与分析流域多尺度景观格局特征的变化提供了全面的研究视角与基础的理论参考依据,使得流域景观的多层次结构体系愈加清晰。此外,Allan[32]在综述已有关于景观变化对河流生境条件和各生物要素影响的系列研究时,提出并强调了以河流为载体囊括流域或子流域、河流廊道、局部河段三类*具代表性的尺度展开河流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图1-2),这也为本书确立不同尺度流域景观多层次结构分析空间单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理论依据,使得从“流域/子流域—河流廊道—局部河段”的点、线、面多尺度系统出发探讨流域景观格局特征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变化规律成为可能。
图1-2 景观格局特征变化的常用研究尺度[32]
1.2.1.2 流域景观格局特征演变研究进展
目前,国内外从宏观尺度分析流域景观格局特征的研究已颇为成熟,常通过对各类自然与人为土地利用类型及其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来反映流域景观在宏观尺度的变化规律[33]。已有的研究常采用转移矩阵分析方法探讨各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移交换变化[34,35],计算各种具有不同生态意义的景观格局指数(如景观破碎化指数、多样性指数、干扰度指数、形状指数等)的大小来表征不同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时空变化的特征与意义[36-38],也有通过构建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的分析模型来预测其未来时空变化趋势的研究[39-42]。但现有的研究中常常模糊地使用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这两个概念。1995 年,Forman[43]提出了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均是由不同类型、大小和形状的景观斑块排列组成的空间结构体。其中,前者强调不同景观斑块的类型和占比随时间的变化,后者则侧重于景观斑块间空间镶嵌结构的变化特征。景观斑块的类型常常用各土地利用类型来表示[44],且研究表明不同位置上土地利用类型随时间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着景观斑块的空间配置特征,即景观格局的特征[45];景观格局的特征又是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斑块在空间维度上结构与配置特征生态意义的体现[46]。这说明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与景观格局变化特征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与重叠性,各有侧重的同时又互相补充,这是研究中经常混淆两个概念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分析宏观尺度流域景观格局特征的变化时,在时间维度要重点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特征,而在空间维度则应重点关注景观斑块的空间配置特征(即景观指数表征的景观格局特征)。
除从流域尺度展开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特征的分析外,部分学者围绕河流本身的线性结构从廊道尺度或局部河段尺度重点分析了不同宽度河岸带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的差异[47-51]。徐海顺等[52]对上海市黄浦江100~800m 宽河岸带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发现300~400m 宽度河岸带的景观破碎化程度*高,100m 宽度范围内河岸带为河流廊道生态保护*重要的区域;吴晶晶[53]对比了福州市城市核心区、边缘区、乡村三个不同城市化梯度所在河段的河岸景观格局特征;徐珊珊等[54]分别分析了北江干流0~10km 不同宽度河岸带梯度下河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特征的差异;Apan 等[55]分析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山谷流域内,不同等级河流水系两侧不同宽度的河岸带景观结构与空间特征的差异;也有部分学者综合了流域、河流廊道或局部河段尺度来分析不同尺度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特征的差异[56,57]。
上述这些研究均主要侧重于描述流域内不同尺度整体性景观格局特征的变化规律,分析不同尺度流域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将流域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看作不同的景观斑块镶嵌综合体以反映不同尺度研究区的景观斑块类型与组成的特征。较少在多尺度综合分析时将廊道或局部河段尺度河流景观的物理结构特征与水文生境特征纳入分析的范畴[58],而它们对于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意义重大[59]。现阶段描述廊道或局部河段河流景观物理结构与水文生境特征的研究均集中在河流地貌学与生态水文学领域,并侧重于运用经验公式或实地调查展开研究,分析河流的形态、廊道结构、连通性、水文生境特征等[60],以作为建立其与河流水文、生态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这丰富并扩展了流域廊道或局部河段尺度景观格局特征分析的内容与角度。
综上,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