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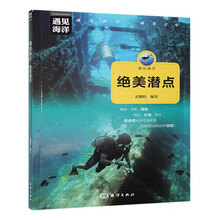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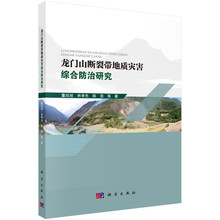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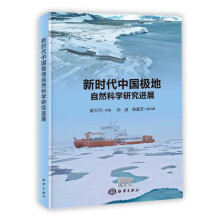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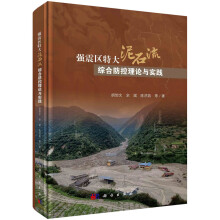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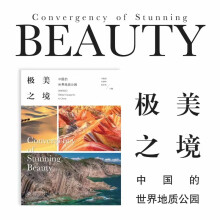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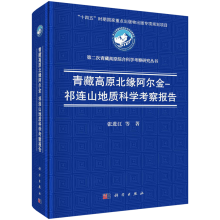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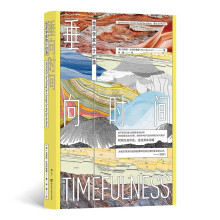
第一章绪论
湖泊是大陆上地形相对低洼和流水汇集的地方,按其成因,湖泊可分为河成湖(如鄱阳湖、洞庭湖)、风成湖、冰川湖、火山湖(如长白山的天池)、堰塞湖、岩溶湖和构造湖等。现在全球湖泊总面积有2.50×106km2,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8%,然而,在中-新生代时期,湖泊是非常发育的。湖泊是大陆沉积物堆积的重要场所,也是有机质富集、埋藏并向油气转化的重要场所,中国目前发现的石油大多数是湖泊成因的。
中国湖盆油气勘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进入重大发展瓶颈期,现阶段中国很难再发现整装高效大规模的常规油气存储区带,必然要走向非常规油气藏的勘探开发(孙龙德等,2010;宋明水等,2017;王华等,2018;朱筱敏等,2019)。近十年来,深水重力流沉积已经成为中国湖盆油气藏勘探和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相继在多个盆地的油气田勘探开发中获得较大突破,如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廊固凹陷、车镇凹陷和沾化凹陷沙河街组,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伊通盆地岔路河断陷双阳组,辽河盆地西部凹陷和滩海地区沙河街组等。
在深水环境中,大多数碎屑沉积物都是以块体-重力方式搬运的。重力流学说已成为沉积学中的重要理论,利用它可以合理地解释深海(湖)砂岩的成因。重力流是深水区域沉积物搬运的重要动力,也是海(湖)底地形的重要改造力。现代湖底调查和古代地层的研究表明,重力流可以形成巨大的沉积体。深水重力流成因砂(砾)岩储层由于与烃源岩直接接触,相比其他类型的沉积储层,含油气性最好。通过对渤海湾盆地不同沉积成因的油气藏进行含油性分析,发现该类油气藏油气充注系数一般为60%~100%(刘磊等,2017;张景军等,2017)。但是重力流成因的油气储层由于孔隙度、渗透率较低,往往形成致密油藏、致密气藏、页岩气藏等非常规油气藏,增加了勘探开发的难度,因此正确认识重力流沉积机理与砂体分布规律是提高该类油气藏“甜点”预测成功率的关键。
中国陆相深水重力流在断陷盆地和拗陷盆地中形成两种特色鲜明的储层类型(袁圣强等,2010;郑荣才等,2012;袁静等,2016,2018;杨仁超等,2017;周学文等,2018)。前者以砂(砾)岩等粗碎屑沉积为主,主要形成于盆地陡坡带深水区;后者以砂岩、含泥砂岩等细粒沉积为主,多为拗陷湖盆中三角洲前缘欠压实未固结的沉积体(物)在重力作用下由自发向下坡运动而形成的,在滑动、削蚀、分流与稀释的过程中,形成舌状和朵状分布的多种类型的重力流沉积物叠合体。
第一节何为“深水湖盆”
对于钻井工程师和石油地质学家来说,“深水”具有不同的含义。钻井工程中的深水是指目的层的钻探井位所处的水体深度,也就是使钻探目标位于深水环境。例如,墨西哥湾深、浅水的分界值为200~457m,美国内务部用“深水”和“超深水”分别表示水深超过305m和1524m。
从构造角度讲,Gore(1992)认为陆架是水深小于180m的范围。西北非洲的大陆边缘,陆架坡折的水深范围为100~110m(Seibold and Hinz,1974)。Hesse和Schacht(2011)为了把海平面低位期的上陆坡沉积排除在外,将水深500m定义为深水。
而地质上的深水是指地下油气储层形成于深水沉积环境(Curray and Moore,1971;Hathway,1995;Famakinwa and Shanmugam,1998;张家烨,2018;赵健等,2018)。在地质学中,对“深水”的定义有很大的争议。在海相环境中,通常“深水”是指水深大于200m范围的区域,向海方向为陆架坡折、陆坡陆隆及海盆环境。然而,对“深水”水深的精确定义并未达成共识,Pickering等(1989)认为“深水”专指风暴浪底之下的环境。风暴浪底的深度并非恒定值,而是随热带气旋风速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在弱气旋期,风暴浪底在20~30m的水深范围,而在强气旋期,风暴浪底可能达到陆架坡折处或者更深(大于200m),使得沉积物可以搬运至陆架边缘之外。也就是说,风暴浪底从20m至大于200m,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湖泊水体深度的研究应该充分考虑反映水动力条件的浪基面、枯水面和洪水面三个界面。由此可以划分出滨湖、浅湖、半深湖、深湖和湖湾五个水体环境(石宁和张金亮,2008)。半深湖环境位于浪基面以下水体较深部位,地处缺氧的弱还原-还原环境,沉积物主要受湖流作用的影响,波浪作用已很难影响沉积物表面,在平面分布上位于湖泊最内部。深湖环境位于湖盆中水体最深部位,在断陷湖盆中位于靠近边界断层的断陷最深的一侧。波浪作用已完全不能涉及,水体安静,地处缺氧的还原环境,底栖生物基本不能生存。
由此可见,在湖盆环境中,深水依然无法用一个准确的深度值来描述,本书建议采用经验法并遵守以下准则来判断沉积是否处于深湖环境。
(1)深湖环境应位于浪基面以下,静水环境是重力流沉积物形成后不被破坏改造而得以保存的必要条件。
(2)水平层理黑色泥岩(排除沼泽环境)是识别深水环境的可靠标志。
(3)丘状交错层理常被用作建立风暴浪底的标准,但其有效性存在争议。
(4)正递变层理砂岩、块状层理砂岩的出现是确定深水环境的合理标志。
与海洋相比,湖泊一般缺乏陆架坡折、陆坡陆隆等构造及潮汐作用,波浪和湖流的规模及强度一般都比海洋小得多。现代湖盆地质调查表明,深水湖盆广泛发育(表1-1),如世界第一深湖贝加尔湖,最深处达到了水面以下1637m。贝加尔裂谷系是在晚白垩世—始新世夷平面基础上由于断裂作用而形成的。断裂作用最大幅度超过10km(图1-1)。在裂谷系中心部位发育的断层长度最大、最深、最早,并以准对称形式向四周扩展。
第二节深水湖盆重力流沉积物基本特点
目前关于深水重力流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其石油地质意义已得到了足够重视,但重力流的流体类型多样和沉积作用复杂,同时深水重力流实验实现难度大,不能很好地对重力流理论进行实验佐证,导致对重力流沉积理解及认识的分歧很大(Bouma and Brouwer,1964;Tibaldi et al.,2009;耳闯等,2010;李相博等,2011;陈世悦等,2017;陈广坡等,2018)。
研究重力流的沉积特点,分析重力流与其他类型流体的异同并找出重力流沉积的特殊性是重力流沉积分析的基础。从物质组成来看,重力流是由湖水(或海水)、泥质物质和固体岩块(包括碎屑和成层透镜体),以及塑性体、未固结的岩层和碎屑组成。这种混合的流体是其他流体范畴内不曾出现的,重力流中各种成分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有变化的。在重力驱动力作用下,在有湖水(或海水)的掺和时,重力流发生整体运动。许多学者都认为重力流是一种高密度流,是块体运动。
根据沉积物在流体中的含量差异,重力流可划分为沉积物重力流和流体重力流。沉积物重力流是在流动过程中重力驱使沉积物运动而带动隙间流体运动;流体重力流是流体因重力而运动并驱使沉积物向前运动。
可以看出,重力流的自身性质及其运动沉积过程都极其复杂,它主要表现在组成、运动方式、运动过程及结果上,具有非牛顿流体的性质,虽然它是块体运动,但是内部质点的运动相当复杂,产生复杂应力,使质点形成复杂的分布,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地质现象。重力流运动的特点,不仅取决于重力沉积物流的内部特征,而且与触发因素、斜坡倾角、水体深度、斜坡地形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断陷湖盆重力流沉积以粗粒径砂(砾)岩沉积为特色,而拗陷湖盆重力流沉积以细粒砂岩沉积为特点。
东营凹陷北坡沙四段深水砂砾岩沉积岩石类型主要包括砾岩、砂砾岩、含砾粗砂岩、细砂岩和深灰色泥岩(图1-2)。砾石成分复杂,以灰岩为主,还有泥砾、碎屑岩砾石。其中近源区为巨厚的砾岩沉积,砾石富集且粒径大,一般在3cm以上,最大可达15cm(数据来自岩心测量),可见少而薄的灰色泥岩夹层。砾岩分选、磨圆差,多为次棱角状,层理不发育,为厚层块状,具有近源快速堆积的特点。砂砾岩底部见冲刷面,泥岩夹层处伴生小型的同生正断层,是断裂带活动的遗留标志。扇体中部为砾岩层与薄层深灰色泥岩层、砂质泥岩层间互出现,砾石粒径相对内扇明显减小,泥岩夹层在岩心中频繁出现,常见冲刷构造和强烈的同生变形构造。远源区为深灰色泥岩夹薄层粗砂岩、含砾砂岩,为扇体沉积末期小型重力流舌状体的延伸(图1-3)。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沉积时期,三角洲前缘砂体堆积过甚后,在外力触发下砂体沿着剪切面呈不规则整体搬运,在前缘斜坡带坡脚处停止滑动形成滑塌砂体(邓秀芹,2011;陈飞等,2012;高山,2017;李华等,2018)。该过程中虽然有滑塌物与周围水体进行了物质交换,但是滑塌物并未被周围流水进行充分稀释,滑动岩体内部变形较少,保留了部分原始的沉积构造,砂岩内部的沉积变形构造是滑塌沉积的典型特征(图1-3)。除典型的滑塌砂体外,延长组深水沉积物还包括含有泥砾的块状砂岩和无层理的块状砂岩,以及灰色、深灰色的正递变层理细砂岩、粉细砂岩,显示浊流沉积物层序特征(图1-3)。
第三节深水重力流沉积理论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目前已发现许多油气田的储层是各种重力流沉积成因的砂岩,这为寻找油气田开辟了新的领域。虽然重力流已受到沉积学家的关注,并开展了许多研究,但至今对它的认识还是不够充分,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重力流研究现状
深水重力流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为沉积学注入了新的血液,解决了长期令人迷惑不解的深海砂体和粒序层理成因等问题,也改变了人们对沉积学研究的传统思维模式。
深水沉积研究经历了70年,争论也持续了70年。从浊流及鲍马序列开始,随着对浊流定义的过分使用,到今天对鲍马序列作为浊积岩相序及相关的扇模式普遍持否定态度,深水沉积研究经历了一个认识的旋回。主要问题和争论的焦点是:①是否所有深水砂岩都是浊流成因;②鲍马序列能否代表浊积岩相序;③是否所有的深水扇水道下方都能形成席状的、平行的、加厚的、具有丘状外形的浊积砂岩沉积;④是否可以利用地震方法识别深水扇的砂岩储层(Allen,2000;Jobe et al.,2010;杨仁超等,2015;Yang et al.,2017;操应长等,2017a;周立宏等,2018;王星星等,2018)。
对浊流概念的过分使用是把深水扇模式内几乎所有的深水沉积都解释成浊流成因,当浊流理论的神话被打破后,曾经为之建立模式的学者纷纷撰文抛弃原有扇模式。尽管浊流及相关的深水扇模式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石油工业界从浊流理论和相关模式中获得了许多油气发现,勘探学家仍然希望通过这些模式寻找更多的油气,科学理论和应用出现了分化。深水沉积研究面临着对过往认识的否定和如何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重要问题(Coleman and Garrison,1977;Bouma,2001;Heron et al.,2009)。对深水沉积过程和流态的认识及沉积模式的建立是当今深水沉积研究的难点,实现深水砂岩储层的有效预测是深水沉积研究的主要目的。
中国对深水重力流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有公开发表的浊积岩方面的文章(李继亮等,1978)。同时,国内外学者认识到了浊流理论在沉积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于1983年召开了全国浊流沉积学术会议,开启了重力流理论在国内的研究热潮,在重力流沉积特征的研究和重力流沉积模式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尤其是很多学者根据其研究区的地质资料,提出了多种指导油气勘探的重力流沉积模式,加上对重力流含矿性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先后在辽河油田、渤海湾盆地等许多地方发现了与重力流有关的油气藏,对国内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重力流沉积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其内部的层序结构、物源方向及沉积盆地水深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还从储层物性、生储盖组合的空间演化与构造的关系来对深水扇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