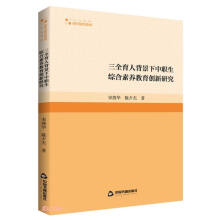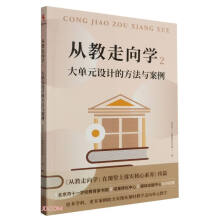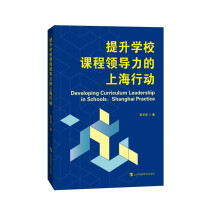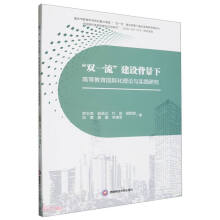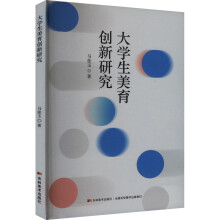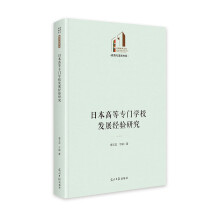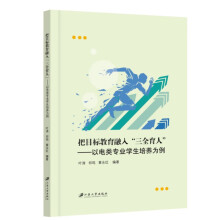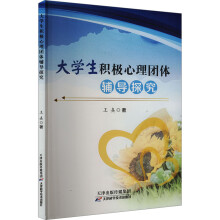《家风与奋斗》: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所以行孝须及时。范仲淹就因早年家贫未能厚养母亲而倍感伤怀,在给晚辈的家书中嗟叹:“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元稹也在给侄子的信中感叹对父母的奉养之日太短:“故李密云‘生愿为人兄,得奉养之日长’,吾每念此言,无不雨涕。”今世之人,尤当注意养亲之事,由于社会经济压力和个人原因,部分成年人不仅未能养亲,反而在生活上依靠父母“啃老”;还有部分儿女常年在外,一年难得回家探望父母一次,养亲更多的是给予金钱帮助,但缺乏亲情温暖;更有甚者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甚至遗弃父母。这些行为与古人及时养亲的思想格格不入,也造成部分人在醒悟过来后,却产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身遗憾。因此,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及时以各种方式孝敬父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每一位当代人都应具备的自觉意识和基本道德责任。
二是兄弟和睦则家必兴。“悌,善兄弟也,从心从弟。”兄弟和睦即为“悌”。曾国藩深知“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的治家大道,因此高度重视兄弟关系,提出“以和睦兄弟为第一”。并且经常对此进行自我反思,在其47岁时还因“去年在家争辨细事,与乡里鄙人无异,至今深抱悔憾,故虽在外,亦侧然寡欢”。颜之推认为兄弟和睦以共御外辱是兴家之基,指出“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躇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况且“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但却失敬于兄、失恩于弟,这种能够与众人相处融洽,却不能与一两个兄弟和谐共处,能够对关系疏远之人广施恩惠,却对骨肉兄弟薄情寡义的行为,是何其的愚蠢和无知,更何谈家业的兴旺发达。
曾国藩不仅自己亲行悌道,还教育子孙要兄弟友爱和睦,认为“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况兄弟乎?”他告诫长子曾纪泽作为“下辈之长”,要“常常存个乐育诸弟之念”,要求他与亲表兄弟之间“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杨椿自己身体力行“同盘而食”“不异居、异财”的兄弟友爱之道,并以此告诫子孙要友爱兄弟,认为子孙辈如果“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在曾国藩看来,兄弟不和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互相谅解,甚至在父母和宗族乡党面前暗用机计,互相争斗,必欲“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他以家乡刘大爷、刘三爷兄弟二人因“皆想做好人,卒至视如仇雠”的事例,说明应当保持“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的心态,兄弟之间“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曾国藩六弟曾国华随湘军李续宾部转战三河镇,被太平军全军歼灭,曾国华战死。遭此大变,曾国藩在给兄弟的两次书信中,沉痛反思“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5,认为完全印证了“和气致祥,乖气致戾”的道理,教训十分惨痛,因此他告诫兄弟们“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力求和睦”,要求兄弟之间若一人有过失,则其他人均应各进箴规之言,有过者则力为惩改。
袁采认为,在兄弟关系中,“长者宜少让,幼者宜自抑。为父母者又须觉悟稍稍回转,不可任意而行,使长者怀怨而幼者纵欲,以致破家”。兄弟和睦虽然少不了兄弟之间的互相忍让,但父母也要因势利导,起到缓和化解矛盾的作用,不能去激化矛盾,否则将招致破家之灾。
张英则从人生喜乐的角度论述了兄弟和睦的重要性,他引用法昭禅师的偈语:“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提出“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若恩意浃洽,猜间不生,其乐岂有涯哉?”的观点,认为人的一生中,兄弟是相伴时间最长的人,若兄弟感情和睦,那么人生也就可以得到最长久的快乐。
三是心无偏私则家必正。同居贵怀公心,心中无偏私,行为不偏向,则家风必正,家庭必和。
在财物方面,要讲究公平,封建大家族往往聚族而居,既有私财也有家族公财,而家庭不和往往就从财物分配不均或私窃公财开始,以致“有一人设心不公”,则“其他心不能平,遂启争端,破荡家产,驯小得而致大患”。而如果“长必幼谋,幼必长听,各尽公心”,则自然无争。2在遗产处理上,“若父祖出于公心,初无偏曲,子孙各能劾力,不事游荡,则均给之后,既无争讼,必至兴隆”。这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有家庭成员在对待财物方面,人人都秉持一颗公心,才能使家庭“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