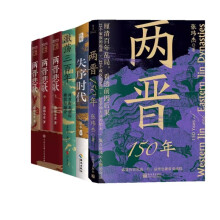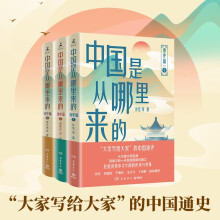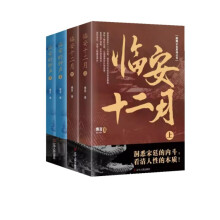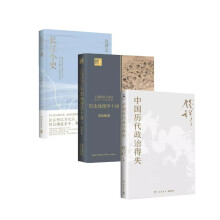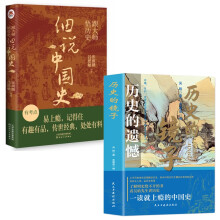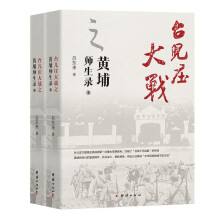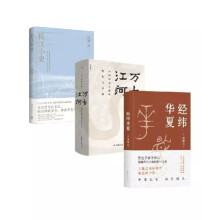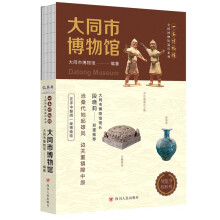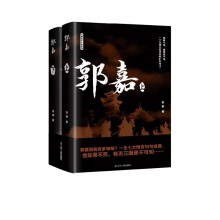在本系列丛书之《汉初战略》中我们说过,景帝刚开始立栗姬的儿子刘荣为太子,可是栗姬嫉妒成性,气量狭窄,经常无事生非,给景帝宠幸的妃子穿小鞋。这些受宠的女人大多是通过景帝的姐姐刘嫖进见的,所以她就把心中的怒火宣泄在刘嫖身上。当刘嫖提出要把女儿嫁给她的儿子刘荣时,栗姬严词拒绝。这刘嫖哪是省油的灯,就在景帝面前揭栗姬的短。这时王夫人(武帝刘彻的母亲)乘虚而入,与刘嫖结亲,两个女人联手,终于扳倒了栗姬,太子刘荣被废。这时周亚夫据理力争,认为太子毫无过错,无端被废会引起动荡,于是景帝疏远了周亚夫。有可能周亚夫说话刚性十足,宁折不弯,也不讲究方式方法,伤了帝王病态而脆弱的自尊心,再加上景帝的弟弟梁王一直对周亚夫抱有成见,每次进京时都要向窦太后讲周亚夫的短处,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周亚夫渐渐失宠。
栗姬被排挤以后愤郁而死,王夫人被立为皇后,刘彻被立为太子。这王皇后有一个哥哥叫王信,这人没有太大的本事,就是酒量“超逸绝伦”。景帝他妈窦太后说:“应该把你老婆王皇后的大哥王信封为侯。”景帝推辞说:“当初的南皮侯窦彭祖和章武侯窦少君(景帝的舅舅,窦太后的兄弟),在先帝(指文帝)在位时都没有被封为侯,等我继位后才加封,所以王信现在还不能被封侯。”这个窦彭祖是窦太后大哥的儿子,窦少君是她的弟弟,这些外戚本身都没什么功劳,就是因为和一个有权势的女人沾边儿,就有了荣华富贵。景帝的意思可能是在自己生前封赏身无寸功的大舅哥王信必定落人口实,新君登位大赦天下时再有所行动应该更好。窦太后说:“君主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必因循守旧。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然不得封侯,死后他的儿子反而得享殊荣,我一直为此深感遗憾。皇帝还是快封王信吧。”景帝没办法了,就说:“这事我得和丞相商量一下。”周亚夫听完景帝的话后说道:“高皇帝规定'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有违此誓,天下人共同讨伐他。如今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兄长,可是身无寸功,若是封他为侯,有违规定,也会引起天下人的非议,这样不好。”景帝默默无语,只能作罢。
按照景帝的表情来推断,他并非不想立王信为侯,只是不想自己亲口说出来,他想让周亚夫提出来,然后他顺水推舟,这样就把自己洗脱干净了,然后让周亚夫承担非议,而周亚夫根本不理这一套,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铁面无私。本来这是以公废私,应大力提倡,可传统政治的“人治理念”有一条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那些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就能得到法外开恩;那些所谓的外人,尽管流血流汗,仍然徒劳无功,有时不但无功,甚至还有错,所以就有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这个王信后来还是被封侯了。根据历史上的记载,这个人最大的“贡献”是促进了消费,主要是酒类的消费。那时,汉朝与匈奴战事不断,匈奴中有一个叫唯徐卢的贵族率众归降,景帝就想封他们为列侯,以劝后人效法,作为瓦解敌军的策略。丞相周亚夫不同意,进言道:“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投归陛下,而陛下封他们为侯,这样我们还怎么责备那些怀有二心、见利忘义的臣子呢?”景帝道:“封唯徐卢等为侯不同于丞相所说的情况,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战略。想招降纳叛、不战而屈人之兵,又不想采取实际行动引导后来者,这怎么行呢?丞相的建议不可采用(景帝实际上只说了最后一句话,前面的话都是笔者根据上下文意思增加的)。”于是把唯徐卢等五人都封为列侯。周亚夫因此谢罪称病,后来又被免除了丞相职务。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并赏赐给他食物,可是宴席上只有大块的肉,没有切碎的肉,连筷子都没准备。周亚夫心里不高兴了,回头让安排酒席的人拿双筷子来。景帝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这难道还不让你满意吗?”言外之意是你这个人要求越来越高,赏你一块肉就已是额外开恩了,还挑三拣四的,不知足?其实景帝这纯粹是试探人,也是没病找病,就想看看周亚夫的表现,屈居人下的都会遇到这种无理取闹的无聊事。周亚夫脱帽谢罪。景帝起身时,他趁机快步走出。景帝看着他的背影,说:“这个心怀不满的家伙,不是将来能全心全意侍奉幼主的臣子。”景帝故意设这么个局,就是要看周亚夫有什么样的表现,周亚夫的“怒形于色”让他动了杀机。汉景帝这么做也是为自己的儿子着想,铲除障碍,因为像周亚夫这种人只有他自己能处置。没过多久,周亚夫的儿子从为皇家制造刀剑盔甲等御用物品的“工官尚方”那里买了五百套将来供陪葬用的盔甲盾牌等器物,那时的人习惯在生前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搬运工辛苦一遭却没有得到工钱,他们知道这是偷买皇家专用器物,一怒之下,就上告周亚夫的儿子购买违禁品欲图谋反。此事在追查的过程中牵连到周亚夫。景帝一直想惩治他呢,这可真是天赐良机。接到状纸后,他就派官吏成立“专案组”,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