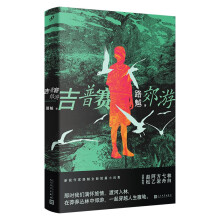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为奴隶的母亲——“左翼”乡土小说》:
现在让我来额外叙述一点我和彭仲甫的过去吧,可是话又拉得太开,请不要厌烦。
去年的“黄祸”,光县算遭得顶大了。不知费了多少戴慈善帽子的电报纸,省里的赈务委员会才派了我带五千担米去赈灾。米是用民船从河里输送去的,直到十二月我才坐了牲口去。
到了离县城不过二十多里的狗尾山,和我带去的那个勤务兵,还有一个挑行李的老头,在那条倾斜的山路上走着走着,突地,那个勤务兵指着前面的树林里叫:
“看,这么冷的天气,干吗前面那人还是个赤膊,他手里拿的什么——刀吧,王科长?”
我伸伸脖子,没瞧见什么。
走了不到丈把地远,那个挑行李的老头也说有人。我再抬头:这回前面山岔里的冬青树底下,有一个瘦长的汉子在探头探脑。远远儿地望去,真像是个赤膊;一手拿一件什么,可给柴草遮住着,瞧不明白。我顿一顿说:
“不妨事吧,这儿去县里很近的。”
我们走过那座林子才一半,大树把天空遮得阴郁郁的,风吹着树叶窸地发响,格外来得清冷。我正在惊讶着这地方的险峻,两边山上猛地发出了几声吆喝。
一转眼,那些树背后的柴草里钻出一二十个人来,可都不像强盗——小孩子和娘儿们占多数。虽然也有几个年青点的汉子向我们走来,可没一个不瘦得鬼一样,像几十年前就没吃过饭,走起路来还打颤哩。
他们手里没有枪,不过是些锄头和柴刀一类的东西,娘儿们抓的还是石子和土块。只有刚才在冬青树底探头的那个家伙,背上背一块麻布,手里拿一把鬼头刀,光着一双火柴似的胳膊,还比较地威武。
他们走了拢来,那个瘦鬼先把鬼头刀向我的勤务兵一晃,吓得他蹲了下去;接着就跳到我的牲口跟前叫:
“给老子留下行李来!”
声音可不大响。
后面的娘儿们在拼命地呐喊着,有些也甩石子过来。我看这样子不对劲,可是一面还在打量着这些强盗。
世界真的变了:连强盗都不像从前小说上说的那种凶的彪形大汉,就只是这样一班货色!不过今儿还算是他们的幸运,碰的是我。要是我们的×委员来么,他的太极拳练得那么好,这些个娘儿们就全换了那个拿鬼头刀的,恐怕他们也不中。
回头再瞧瞧我的勤务兵和那个挑行李的,该死,这两个家伙像发了疟疾,抖得那样厉害。唔,好汉不吃眼前亏,虽说只有这几个小毛贼,可是犯不上着了他们的道儿,几件行李算得鸟事,我就统统扔给他们。
后来有一个小鬼头见我穿的是件皮袍子,说要剥猪猡,我就简直使了性子,自己脱掉扔在地下,穿一件短棉袄走了。
我刚爬上那个山坡,回头一瞧,马上又在后悔,原来这些家伙的目的,都不像是来劫行李。他们把我撵跑了,就抢起那个网篮里的饼干来,还有盐食盒子里的咸菜。我在山上听得一个小孩子在骂饼干给人抢了去,吃了会要拉痢的。大概他们都是饿慌了才来做这玩意;早知道如此,我就是一个人也该使他妈的一下劲,给这些家伙一点儿厉害尝尝。现在后悔有鸟用。再转去?懒爬得山。
那天下午,我就是这么着穿了一身短打进的城。全城都知道我在路上遭劫的,商会派了彭仲甫做代表来欢迎我。那家伙和我一见面就像个几十年前的朋友:说起话来一点客套没有。其实我和他虽是只隔得八里路的同乡,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晚上,彭仲甫在自己开的明远药房摆接风酒。我的凳子还没坐得热,他就叫一个学徒到衣庄里去买一件大衣和一件皮袍子给我。我告诉他手头没有钱,他说:
“再没钱,不穿衣可不成,我帮你给了,回头还给我去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