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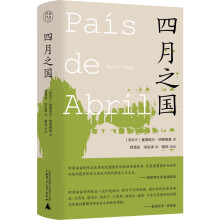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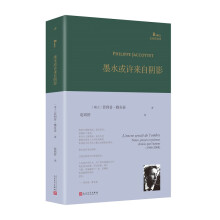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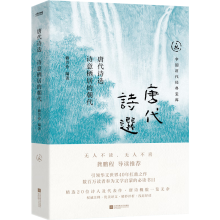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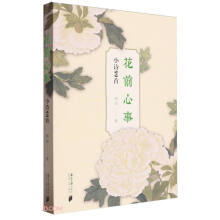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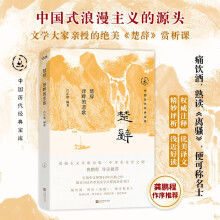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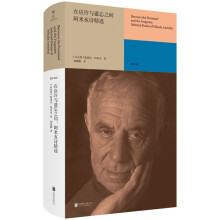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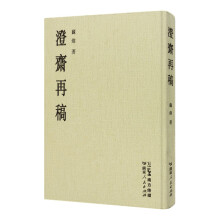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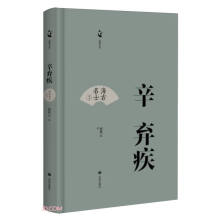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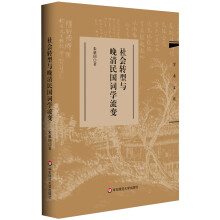
学数学的人爱好并操习古诗,尝试用计算机为工具对古诗创作开疆辟野,谓之新古典主义。能否成立,请读者方家判评。
总论:艺术革命的结构
——源于自然、融汇自然、创造自然
作品是自我的投影,因为人是活在情感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遍读中西方诗人、文艺家传记与艺术史的基础上,我参考托马斯·库恩基于群体演进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创构了一个基于个体演进的“艺术革命的结构”,作为本诗集与我的诗论艺术论的框架。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超凡脱俗的最高追求,其区别我赞同哲学家尤格·闵斯特堡认为的关联与孤立,即科学是共同体的合力,艺术是自足孤立;科学有上下继承,而艺术永不重复前人;科学发现一旦完成则后续是重复,而艺术创造需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把人类历史上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所有演变高度抽象,化约为三:
起点,是源于自然。人生下来首先是大自然的一个动物,当然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能创造和使用抽象符号的动物。此境天工开物,其成功是对天赋才情的褒奖,诗界如二十多岁的王勃的《滕王阁序》、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过程,是演化与内卷的双螺旋结构(evolution involution,或曰:人出生与成长的终点是死亡),我称此过程为融汇自然,其间使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符号系统,我概之为四:古今之间、中西之间、科技与人文之间、天人之间。此境需艰苦砥砺,或曰匠心,或曰人力;其层高之最,我设为“杰出”;其人,我定名为“大师”。
最高境界是人类中的极少数,截断众流、自辟宇宙、但立新规、开宗立派,我称之为创造自然,或曰革命(revolution),即创造出了自己的符号系统或语言系统,我定义此境为“伟大”量级,其人定名为“天才”。中华诗脉之屈陶李杜苏,西方诗脉之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翁悲剧、歌德《浮士德》。它是在艰苦砥砺之上的天赋才情在特定机缘下爆发出的原始造化之秘,是前两境“天工”与“人力”的正反合,我称之“夺
天工”。
第一境,源于自然,“天工”
在所有的天工开物中,我认为淳朴真挚,以及衍生其上的爱与自由、大爱大悲悯是通往伟大的第一天赋。儒家如《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道家如《庄子》所谓“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西方如托尔斯泰所谓:没有单纯、善良和真实,就没有伟大。
由此方接续《诗大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于是“情动于中”之情才是真挚真情,再后“修辞立其诚”“而形于言”,哪怕白描不修,却也天姿神韵,如此,作品才有兴发感动人心的力量,甚至,诗人个人的情感超越自我而成为人类之情感,乃至形成感动千载生命之力量。
其实,孩童的单纯是天性,天性中蕴含的各种能力、各种情感、体验和思想须在社会历练中方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但人一旦步入世俗社会,熙熙攘攘,名利权位,久居鲍肆,不闻其味,未必能正反合而复归于成熟的单纯。
中华文明直到魏晋才形成了艺术自觉。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谓之“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他用“幽情”把超凡脱俗之情怀寄托于斯,这种自觉其实就是用一个精神活动来寄托人生的最高价值,寄托人生对社会的疏离和对世俗的超越。
以此艺术自觉向前溯源,孔子创立的“仁”、老子创立的“道”,均可视为一种艺术之境,即我将艺术广义定义为对个体最高精神价值与终极关怀的形式寄托。于是乎作品至高至大之道,当是保持一颗率真的童心,当仁不让,直道而行,由此方生发出阔大的格局、宏大的愿景和承担巨大风险的创作勇气。
第二境,融汇自然,evolution-involution双螺旋,“人力”
诗心之本色是淳朴真挚,对自我真,对他人真,对万物真,对天地真,如斯自由因真而至,在人文理想与人类梦想之上,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探索,其根基是一颗包容的诗心,包容是通往一切自由之路,它是阔大格局与宏大愿景的种子,从润物细无声之同理心、共情力,到不断提升灵魂的高度与情感的浓度,最终长成普度众生之大爱大悲悯。
此境人力,笃行砥砺。我的体会是四大融汇:古今之间、中西之间、科技与人文之间(所谓科学精神是求真求新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求美求善的科学精神)、天人之间(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之实体世界与自己的心灵世界)。如此海纳百川,格局方阔;如此壁立千仞,境界始高。
其因,唐人刘知几曰史家有三长,不妨扩之为人有三长:才(天赋)、学(后天)、识(才与学的正反合)。诗人艺术家多以天赋才情驱动,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谓之“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严羽也强调“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即艺术家也应是学者,中华文明天赋最高的诗人是李白与东坡,但如果他们没有读破万卷的文史哲根基,任何一个人的天赋才情都不可持续。
所以对标自由,调配职涯,丰富阅历,铸强功底。如经历技术向善、学术求真、艺术尚美等多条生命曲线,经历烟火人家方方面面甚至困顿苦难,遍访大自然及古圣先贤故居谪地,从而磨炼出驾驭多领域的博大才华及在专业领域诸体皆善、诸题兼驭的全能性,诚如清末学者杨守敬所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最终,“灵心圆映三江月”,“笔阵横扫千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