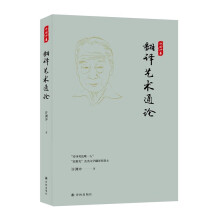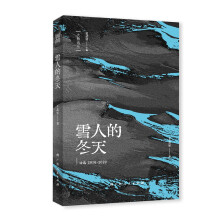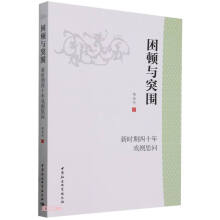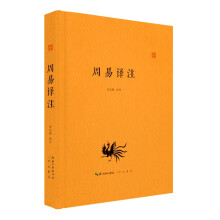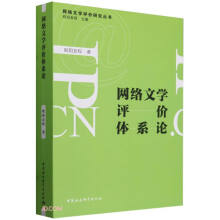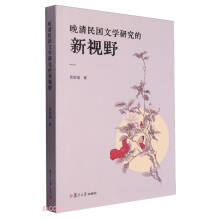第一章
塔克拉玛干的呼唤
策勒告急!县城面临第三次搬迁
对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南缘的策勒县来说,漫天沙尘的日子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这里的春夏两季,每年都有一到两个月的沙尘天气。
在策勒县的历史上,沙尘暴的残酷侵袭,已造成县城两次向南迁移。第一次是在一千七百年前,当时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一个叫“乌丝塔提”的地方,距离现在的策勒县城有80千米。由于风沙的无情侵袭和严重干旱的困扰,县城不得不向南搬迁到一个叫“热瓦克”的地方。虽然“乌丝塔提”古城早已被风沙侵袭,但从那些依稀可见的残垣断壁,以及散落的红柳篱笆和胡杨木桩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在那里生活的痕迹。第二次是在清朝年间,同样的原因,策勒县城又从“热瓦克”搬到现在的位置。虽然“热瓦克”距离策勒县城仅有10千米,但和时间更久远的“乌丝塔提”相比,“热瓦克”留下的遗迹反而更少,它早已被无情的风沙掩埋,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热瓦克”消失的主要原因偏偏就是它距离现代文明太近,而被过度资源开发和人为毁坏。但它的名称和地理位置已被人们所熟知,并载人县志。到了1982年,肆虐的风沙再次逼近县城,当时风沙已吞噬了2万多亩良田,迫使400多户农民离开家园迁往他处,风沙的前沿,也就是离县城最近的沙锋仅有1.5千米。风沙再次兵临城下,策勒县城已岌岌可危,随时面临第三次搬迁。
在一部描写策勒风沙的专题片里,我看到过这样凄凉的画面:策勒县农民买买提-吐逊指着已被风沙掩埋,只露出屋顶的老房子说:“我原来的房子有2.5米高,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家过去那干净整洁的院落,里面已经堆满了黄沙……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当初他们被迫离开家园时的无奈心情……
是沙进人退,向风沙屈服,还是坚守阵地,向风沙宣战?策勒县已面临生死抉择。
此时,在中科院吐鲁番治沙站(研究站)里,有一个人正在他的沙漠植物园里精心培育着他的各种红柳苗子,他就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治沙专家刘铭庭。他不知道那远在1300多千米外的策勒县在等待着他,那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在呼唤着他。
吐鲁番是有名的“百里风区”受灾区,在过去年复一年的岁月里,风沙给吐鲁番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刘铭庭是治沙站的负责人,他带领治沙站的科研人员和吐鲁番人民一起组成了治沙大军,开始了对风沙长期的科学治理。
1969到1982年,在刘铭庭担任吐鲁番治沙站负责人的十多年里,曾任自治区主席的司马义·艾买提,只要来吐鲁番,就要到吐鲁番治沙站看望他们。因此,他对刘铭庭的情况十分了解,并对他们治沙站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其实,刘铭庭早在1972年就已经认识司马义·艾买提主席了,当时拍摄《吐鲁番怎样防风治沙》专题片时要用直升机,需要自治区领导批示,于是他就找到了时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的司马义。虽说两人仅是一面之交,但因为刘铭庭当时在吐鲁番治沙工作方面很有成就,又是直接战斗在治沙一线的科研人员,所以他给司马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2年2月,司马义·艾买提主席又一次来到吐鲁番治沙站,这一次他可不是来表扬刘铭庭,而是来给他下任务的。
司马义·艾买提的出生地是策勒县策勒乡十八大队,也就是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最近的那个村庄,他的家乡已被风沙掩埋,村子里的人也被迫四处逃离。风沙掩埋了村庄、田野,又开始向策勒县城逼近,策勒县城危在旦夕。可想而知,作为自治区主席的他,看到家乡的遭遇,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司马义·艾买提让刘铭庭在吐鲁番站抽调得力人员,前往策勒县组建新的治沙站,并要求刘铭庭他们在三年之内必须治住流沙,保住策勒县城。刘铭庭向司马义主席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刘铭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来到策勒县组建新的治沙站的。
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