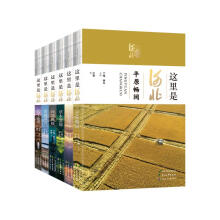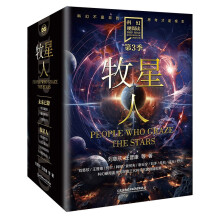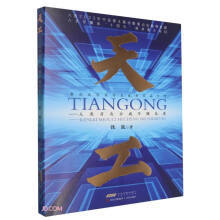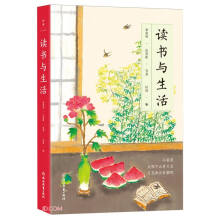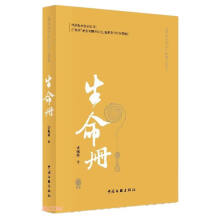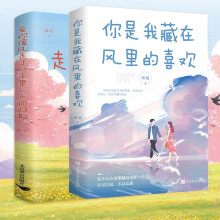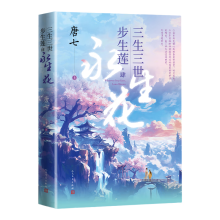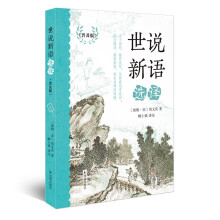(二)信笺嵌入:书信体小说的语体
书信与小说的互渗首先表现为书信对于小说文本的嵌入,即书信“格式”对于小说文本的渗透融合。书信“格式”一般有称呼、正文、结语、署名、日期,它们完全融入现代小说,以小说为“体”,以书信为“形”。
庐隐的《或人的悲哀》是典型的书信体小说,由九封信组成,每篇有同一称呼“KY”,然后依次是正文、结尾,署名也是同一人“亚侠”,最后是不同的时间日期。它是一部标准“格式”的书信体小说,即“完全信札,这普通叫做第二人称”①。但五四时期,“完全信札”的现代书信体小说并不多见,大多数只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而当“外的叙法不成功了的时候,于是结构里的一个人物寄给别个人物的信札,通过这个难关”,②于是就表现为文本中频繁“嵌入”信笺或留言条,“嵌入”的部分篇幅较短,不一定有称呼、署名等“格式”。这种“嵌入体”在整体上影响小说并产生了新的文本结构:一是嵌入的信笺书条具有互文意义,即不同人物之间的信笺及同一封信笺与小说叙述文本具有文本间性;二是嵌入的信笺书条具有语体的直率性,即措辞的随意性和语调的丰富性。庐隐的小说《曼丽》融合了书信和日记两种文体元素,是由曼丽写给沙姊(既是叙述人也是主人公“我”)的一封书信和十一篇日记构成。该小说的叙述结构是:主人公“我”和朋友彤芬回忆起旧相识曼丽,然后阅读曼丽的书信,再细读曼丽的日记,最后又回到“我”和朋友彤芬的现实中——“彤芬也很觉得疲倦,我们暂且无言的各自睡了”①。这是个“圆型”叙述结构,由这封书信统一了“我”和彤芬、曼丽的相似心境,并共同参与了“哀婉之情”的叙述和体验。其媒介就是这封呈现给沙姊的“书信”,它既可视作是曼丽写的信,也可说是彤芬写的信,甚至还可以说曼丽就是沙姊的化身。于是,“我”、彤芬与曼丽具有了同一性意义,引发了人物与读者的共鸣,这正是庐隐小说书信“嵌入体”的价值所在。
郁达夫的书信体小说《空虚》颇有意味,以第三人称叙述,开端展示的是一篇约440字的书信,收信人不详,年轻的主人公质夫认为它是“一张小说不像小说,信不像信的东西”,②点出了其内容的纪实性和虚构性。然而,无论其真假皆关涉主体的生活遭际和生命情怀,如信笺内容开端即写道:“啊啊,年轻的维特呀,我佩服你的勇敢,我佩服你的有果断的柔心!”③主人公质夫的情感经历与维特十分相似,唯有以信笺形式展示出来才更加真实感人,如若让主人公直接叙述则失去了情感性和感染力。郁达夫的另一部小说《茑萝行》实际上是一封夫妻间的情书,充满着温情脉脉的忏悔。它采用信笺“嵌入体”形式便容易指涉叙述人与现实生活中夫妻命运间的互文意义,这能从信笺的展示内容与小说的语言修辞中见出。“茑萝”本乃植物名称,《诗经》曰:“茑为女萝,施于松柏”,④茑乃桑寄生,女萝是菟丝子,二者皆寄生于松柏,以喻亲人相互依存,“茑萝行”亦有“夫妻行”之意。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编撰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时收录了《茑萝行》,标题是《紫藤与茑萝》,文首有“茑为女萝,施于松柏”,开篇即有“不幸的妇人”之书信体格式的称呼,这便为“夫妻行”作了一个注脚。可见,《茑萝行》是夫妻间互相劝勉和表达爱意的生命之书,它比以第一人称直接叙述夫妻关系的小说更为真挚感人,这正是书信体小说的文体价值所在。
冯沅君的《隔绝》《慈母》《误点》《林先生的信》《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EPOCH MAKING》等皆为信笺“嵌入体”小说。她与前面几位作家的叙事形式有所差异,主要以第二人称倾诉式的叙述方式来表现情感的含蓄性和内敛性。《隔绝》是主人公在现实“隔绝”困境下写给情人“士轸”的一封情书,但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是汩汩细流,毫无澎湃汹涌之势,更无“啊啊”“唉唉”的凄凄切切之感,如结尾写道:“我的表妹来了,她愿将此信送给你,并告诉我这间房的窗子只隔道墙就是一条僻巷,很可以逾越。今晚十二时你可在墙外候我。”①对于穷尽机会好不容易能见上情人一面的主人公来说,这等冷静言语似乎不是来自主人公,但也正是这种措辞内敛的“嵌入体”信笺恰恰标志了主人公爱的清醒和坚定,所谓“隔”而不“绝”。《误点》也是一篇以第二人称叙述的书信体小说,展示一对恋人通过信笺告别的场面,男主人公渔湘态度极其坦然,从衣袋里取张“信纸”交给女主人公,女主看完信先是质问、然后劝告、最后哭泣.渔湘便叹了口气,推开她扬长而去。“信纸”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制衡着主人公的情感走向和表现方式,由外到内层层展开,呈现了一种极其内敛而逼真的情感状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