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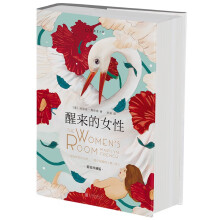


3
……
所以呢,我名叫萨义德,萨义德·拉比诺维奇。我母亲名叫朱迪斯,村里人都叫她“拉比诺维奇家的朱迪斯”。她头上总围着一条蓝色的头巾,手上总飘着柠檬叶的香味。母亲左耳的听觉不好,谁要是在她左边念叨,她一定会火冒三丈。
没人知晓我父亲姓甚名谁。我是个私生子,三个男人都声称是我父亲。
从摩西·拉比诺维奇那里,我继承了一个农场、一间牛舍和一头金发。
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给了我一幢好房子、一些好家具、几个金丝鸟笼以及一副小溜肩。
至于牛贩子格洛伯曼,我的一对大脚和一笔财产都是拜他所赐。
尽管身世如此复杂,令我饱受其害的罪魁祸首仍旧是我的名字。在村里,乃至于整个山谷,我都不是唯一一个生父不明的孩子。不过举国上下——甚至整个世界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叫“萨义德”的孩子。在学校,他们都叫我“玛士撒拉”,要么就是“老爷子”。每每我回家找母亲抱怨,问她为何给我起这么个名字,她总是淡然道:“若是死亡天使降临,见到一个以‘祖父’为名的孩子,肯定立马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错,继而转向别处。”
别无选择,我只好乖乖认命,坚信这个名字能保佑我大难不死,因而也变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甚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那些原始的恐惧也与我全然绝缘。
我大大咧咧地把手伸进鸡舍裂缝里的蛇窝,那些蛇都晃着脑袋盯着我出神,却没有一条张口咬人。
我时常爬到牛舍顶上,闭着眼睛沿着瓦片铺成的斜坡乱跑。
我壮着胆子往村里拴着的狗跟前蹭。这帮家伙常年受着束缚,早就渴望见点血腥,出口恶气。就是它们,见了我也是一脸喜色,摇头摆尾,还会舔我的手呢。
八岁那年,我爬树去看乌鸦的巢穴时,被一对乌鸦袭击,前额重重地挨了一下,我眼前一黑,摇来晃去,一下子没抓住树枝,昏昏沉沉地掉下来,心里却还美滋滋的。周围舒展的树枝减缓了我的下落。着地时,接着我的是厚厚的树叶,松软的泥土,还有我母亲的迷信。
我起身跑回家中,母亲在我的伤处擦上碘酒。
“死亡天使办事很有章法。他拿支铅笔,再拿个本子,所有的事都记录在册,”母亲笑了,每次我得救,她都会这样笑,“不过,沉睡天使却不可靠,他什么都不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有时他会来,有时他却自己睡着了,忘记过来了。”
……
时光流转,我自然而然将母亲的话信以为真,觉得那名字中藏有神力,也为此采取“措施”,预防神力的流失。我曾有过一个女人,几个月共同生活中我们从未行欢,她变得绝望,觉得不可思议,最终离开了我。
我告诉她:“儿子生孙子,孙子会招来死亡天使。”
她先是大笑,然后发怒,最后离我而去。听说她嫁给了别人,却无法生育。但听说之时,我早已对命运的捉弄与玩笑司空见惯,内心掀不起丝毫波澜。
就这样,那名字让我躲过了死亡,也躲过了爱情。但这与我母亲的故事无关。而故事不同于现实,唯浓墨重彩方得以流传。
讲述之中可能会掺杂一丝伤感,但这并非我一生的主调。和所有人一样,我时不时会为自己营造一些哀伤的时刻,然而对生活的喜悦我也深有体会。时间是我自己的,而且如之前所说,三位父亲对我也是宠爱有加。
牛贩子格洛伯曼留给我一笔钱和一辆绿皮卡。
育鸟人雅各布·沙因菲尔德留下一幢漂亮的大房子,这幢房子就坐落在提翁的橡树街。
还有村里的一处农场——摩西·拉比诺维奇的农场。他仍在那里生活,农场却已登记在我名下。他住朝街的老房子,我住院子里惬意的小屋。那小屋以前是牛舍,墙边三角梅蜿蜒盛开,仿佛艳丽的鬓角;燕子振翼求爱,在窗边流连;墙壁的裂纹中依然渗出牛奶的柔香。
旧日里,这里有鸽子低鸣,有母牛产奶。水罐上积着露水,尘粒披金起舞。一个女人曾住在这里,在此欢笑、做梦、工作、哭泣。在这里,她将我带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整个故事。或者换个世故之人的刺耳闷声说来:说到底,就这么回事。从此之后,由底线向上,所有顺嘴言说的细节,无非是为了满足好奇与八卦这对栖息于人类灵魂,如饥似渴的小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