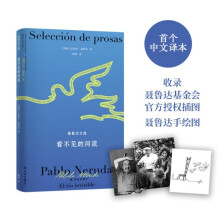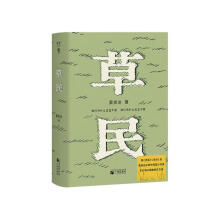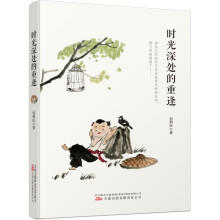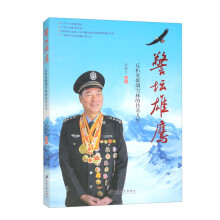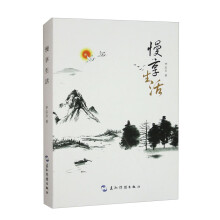初秋的兰州,天空晴朗,秋风送爽。
1961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3点钟光景,甘肃日报社人事处副处长史秀杰和报社办公室秘书孙民,坐着师志清师傅开的吉普车来学校接我与王殿到职,真让我俩喜出望外。因处生活困难时期,各业萧条,寂寞冷落,这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困难,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了自然条件、生活条件都不好的边远县;而我俩却有幸被分到了人人向往的甘肃日报社,而今天又有领导乘车来接,确实令人想不到,给人幸福感呀!也确实令送行的同学另眼相看,从心底十分羡慕呀!由于我们早把物品归总一起,有所准备,我和王殿就很快携行李物品上了车,与同学们难分难舍地告别,离开了曾熟悉的学校。
当时兰州的大街上行人稀少,汽车开得飞快。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们就乘车进了甘肃日报社大门。此时甘肃日报社大门离马路约有几十米远,得上一个缓坡。我心情无比激动,心想,那顶端有着“甘肃日报社”五颗大字的大门早令人向往,那分列两旁的大红柱早对人有强烈吸引力,而从今后就与我们朝夕相处了。
汽车停在了大门东侧的路上。我被分到了下边一排平房的一问房子住,王殿分到了台阶上那排平房的一间房子。室内陈设虽简单,除了平展展的床板,但有一供专用的桌椅,电灯光明亮,感到便于学习,甚满意。
放好行李后,我即迫不及待地走出房间观察了四周环境,看到进报社大门东侧是我们住的这上下两排平房,西侧有相对的两个小院。正迎大门上办公大楼的路,也就是一个大高台台,宽七八米,有五六十层台阶。在东侧,就是我们住的那边,也有一通往上边较窄的台阶路。宿舍东边不远有一自来水管,再远十来米处是男女厕所。我以为这对我们倒也方便。
我正年轻,精力旺盛,便又跑上去眺了两眼上边的情景,看到有一别致的小楼,有几问平房连着食堂,还有一个礼堂。特别是办公大楼非常壮观,非常气派。见空地不多,树木茂盛,到处是苹果树,树上已挂满了苹果。据说办公大楼的另面有印刷厂,有些职工宿舍,有一片菜地,还有一个后门。但当时没去看。总之,无论看哪儿都给人亲切感,令人兴奋。
第二天,孙民向我和王殿介绍了编辑部有哪几个具体部门,问我们愿去哪个部工作。王殿说他喜欢跑农村,愿到农村部。我是一贯喜欢文艺的,就想当文艺编辑发挥专长,即表示愿到文化部编文艺副刊。报社很快满足了我俩的愿望,我就开始了编“百花”副刊的生涯。
第一篇文艺随笔上甘报
1961年9月,我怀着雄心壮志走上了“百花”文艺副刊岗位,自认为自己从在保定上中学时就已经给几家报纸写稿了,又经兰大中文系的锤炼,是能够胜任这编辑工作的,一坐下就开始选稿编稿工作了。清楚记得,第一篇编发的稿件是柯杨的文艺随笔《也谈诗的直率》(柯杨系笔者学兄。后为兰大中文系主任,民俗学专家)。
我在工作中逐渐发现,来稿中的文艺随笔谈技巧的多,强调加强政治思想的微乎其微,而这方面的稿件是副刊上极需要的。因而我从《革命烈士诗抄》中找到灵感,便很快写出了《欲作革命诗,先做革命人》一文。本文2000余字,文笔凝练,富有激情,通过对杨超烈士、刘绍南烈士的两首革命诗的深入分析,告知人们“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诗是真实感情的真实流露,是自身人格的必然体现,所以“欲作革命诗,先做革命人”。经部主任签发,即登载在了1961年12月17日甘报“百花”副刊版。
此篇文艺随笔上甘报,才是笔者来甘报三个月光景,又属第一次上甘报,令人十分高兴,也增强了当好文艺编辑的信心。因而本文也就成了我的第一桩“甘报乐事”。
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