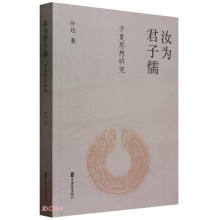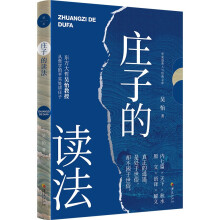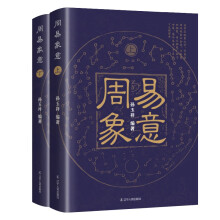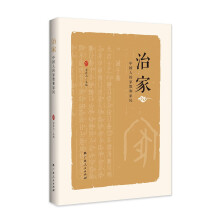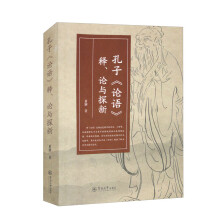《王廷相心性思想研究》:
程颐针对杨时之问而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其本来的目的是要厘清墨家兼爱说与儒家仁义之道的分际,其伦理的意味是很强烈的。但是,要应对有丰富形上思辨性的佛老之学的挑战,仅限于从伦理的角度去阐发理一分殊的意蕴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开显儒家仁义之道的形上根基。朱熹把《太极图说》与《西铭》结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显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与此同时,理一分殊说也具有了比原来程颐提出这个命题时丰富得多的意蕴。陈来在谈到朱熹对于理一分殊命题的发展时说:“一个哲学命题开始提出的时候其意义有时是比较具体的。而一个哲学命题一旦取得了一定的文字形式,以后的人们便可以在文字形式允许的范围内从不同角度或方面去理解它和运用它,从而超出提出它时的具体意义。特别是由于文字的多义性使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超出了按照文字形式所规定的意义范围去运用前人思想资料。”事实上,在朱熹而言,理一分殊不仅是指普遍的伦理原则与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还指本体与现象、一与多、普遍性与特殊性等之间的关系。理一之理已经不只是一个普遍的仁爱之伦理原则,而是成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和变化的形上根据;分殊也不仅是指具体的伦理实践,还指与形上之理区别开的所有形下界的存在,理一分殊命题在朱熹已成为一个包含着丰富的多层次内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智的认识论与德的修养论相统一的本体论模式”。
纵观理一分殊命题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的意义,至少有这样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理一分殊之“理”乃形上之理,理一与分殊所涉及的是形上和形下、本然和实然的问题,理一属于形上界,分殊属于形下界,理一分殊的这种形而上、下之划分使得儒家仁义之道由形下界升至形上界的同时,也使朱熹之形上学笼罩着道德化的色彩,这与其形上学的构建是通过道德的进路达成有关。也就是说,虽然朱熹在用理一分殊来论证世界的统一性时采取了客观描述的方法,但其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问题,而是由人的生命存在参与其中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问题,是着重于存在与价值的统一而归向价值问题的。
朱熹认为,天地万物皆有当然之则,这是天之所赋而非人为的自然之理。人立身处世,遵循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当然之则,这也是自然之理。有学生曾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朱熹答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
理是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所以然之故可谓客观规律,所当然之则可谓道德原则。当然,自然界的事物是不可能遵循什么道德法则的,但在朱熹而言,问题不在于自然界是否存在道德法则,而是要指出,物之存在必有其所以如此存在的理由,有其所以如此存在的条件,若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物之存在就是不可能的。朱熹说:“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这是认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所得之理”)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之存在条件亦可谓当然之则。如果从存在的整体性来看,本没有所谓的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的划分,但朱熹做出这种划分,目的是从本体论的高度为现实的事亲从兄等伦理行为做出说明,将人的自然性存在统合到价值论上,以伦理道德上的应然统摄人的自然性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朱熹这种合所以然与所当然而为一的论证中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合目的性原则,朱熹说“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一方面,物之生成与存在皆是理之所为;另一方面,物之现实存在又无不体现着天理之当然,表征着天理的完满性与至善性。朱熹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若无太极,便不翻了天地”,又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这说明,太极作为天地万物的内在本质又并非某种实体,而是一极好至善的道理,既是天地万物之获得存在之现实性的依据,也是万物所应趋向的标准。“原‘极’之所以得名,盖取枢极之义。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以枢极、万物之根为言,强调“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存在论事实,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宇宙的生化因为有了太极的主宰,才使得世界有了秩序,也具有了价值属性,而万物的生成与存在只有在展现出这种秩序性并不断地趋向于“万善至好”的标准时,才可说是现实的,而且其自身也就获得了无尽的生机,就此而言,朱熹所谓理一之理不单单是体现了万物之统一性,也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牟宗三对于朱熹“理生气”的解释可谓确当,牟宗三认为朱熹“理生气”的“生”并没有生成论上的产生之义,其内涵“不是从理中生出气来,只是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就人言,则是依这理引生心气之革故生新。心气通过其心知之明之认识理而向往理而依之,则引申(似应为‘生’,引者注)心气之合度之行,不依之,则昏沉堕落而暴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