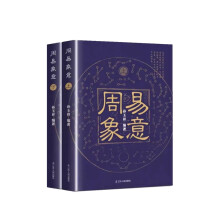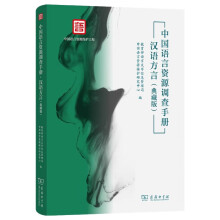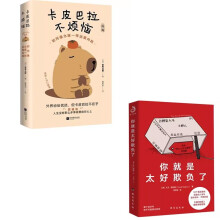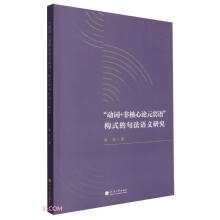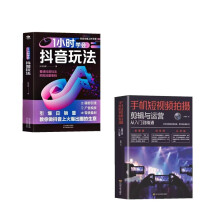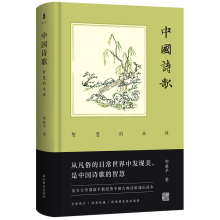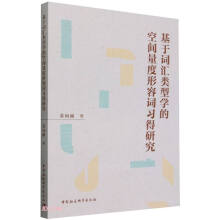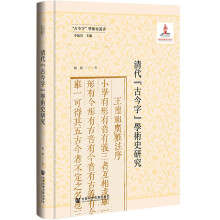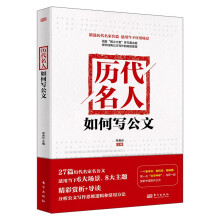第一章 导论
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翻译教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课题,即译者主体对客体(文本意义)的识解过程以及语言文化和思维差异导致的翻译问题及其对策、视角与方法等。王宗炎(1984)认为,翻译的本质在于辨义,但“义”不能反映客体全部的本质属性。文本意义可分解为概念与句法结构的基本语“义”和语境赋予的各种含“意”,二者互为依存,因此语言学和翻译学所论的“意义”实质上就是“义”与“意”的综合体(简称“义—意”)。笔者认为,“辨义为翻译之本”宜修正为“‘义—意’形态识解为翻译之本”。无论是哲学研究或语言哲学研究,或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修辞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现象学、语言哲学、文学等学科理论,“义—意”形态都渗透其中,是一切研究问题的起点,而探究其本质特征与认识规律则是终点。翻译学科理论发展及其跨学科理论视角的一切问题都离不开对“义—意”的辨析。就翻译研究而言,译者对客体的这种“义—意”形态辨析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识解活动,关涉对各种思维运作机制的认识,故成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脱离了对各种“义—意”形态识解与表达的认知机制研究,翻译理论有可能成为一堆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会成为无本无源的纯主观的、思辨性认识,对翻译实践则失去实质性的指导意义。
从宏观认识层面看翻译活动,对“义—意”形态的识解与表达可视为“解码—编码”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或可描述为“理解—表达”的跨语言文化交际的两个阶段。刘宓庆(1999:85)用翻译中的“解码—换码模式”表述翻译理解与表达的认知思维过程,他认为理解所进入的深层系统就是获取源语的信息系统,并将其深层概念系统转换为目的语的深层系统。从认知思维角度看,理解与表达过程并非如此简单。无数的翻译实践过程证明,从理解到表达并非简单的信息系统的获取或概念语义解码与换码的两个阶段,其间还必须经历一个自证或他证的认知思维活动过程,两个阶段之间还有个中介环节,那就是“解码(理解)—自证/他证—编码”模式,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连续统(曾利沙,2014a:59)。本书第五章将重点阐释该模式的特点及通过认知翻译过程研究表征的各种认知机制。
语言符号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人们直接或间接地体验各种社会历史文化生活形态而获得的经验和理性认识,既有传承性又有独*性。前者体现为一个民族语言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后者则不断赋予语言文化以新的生命,推动着社会发展。思想只有通过语言符号的编码进行有序的、符合规范的组织才能有效地进行传播,在人际交流中达到符合预期的沟通。从微观认识层面看翻译活动,译者在解码或理解之维阶段中,首先还必须还原作者本人的“编码”过程。原作的编码是指作者将自己通过观察和体验,对各种生活现象形态和本质特征及各种联系的感悟、思考和认识进行概念化或有序结构化的过程,其思想内容被蕴含或浓缩在主题或话题统摄下的形式结构中,且不同作者都有自己比较独*的创作风格和表达方式。王寅(2005:17)从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观出发,指出翻译具有体认性,这种体认构成了不同语言之间具有互译性的认知基础。翻译的体认性既表现为原文本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又体现出译者对原作者的体认方式和原文本语言形式与内容的认知和理解。笔者认为,译者主体的解码或理解过程本质上包括了对原作者编码的识解过程;或者说,翻译活动解码的一个前提就是译者在理解原文的“义—意”形态时,必须将文本中概念化了的语言符号及其有序结构形式的内容还原为特定的生活场景,即回到文本语言符号所激活或指向的特定生活形态,再考察作者是如何通过观察、叙述或描写视角艺术性地将生活场景和自己的创作意图转化为荷载各种概念“义—意”形态的语言符号。缺失了这一前提,任何译者若只凭双语词典释义或词典译文和自己掌握的双语语法知识及规范,都难以获得对原作文本思想内容完整正确的理解和表达。
然而,表达思想的语言虽然反映和摹写生活,却并非完全直接地表达社会生活现实,语言和社会生活现实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隔阂”,需要译者或读者去补充、充实、完形,甚至参与建构文本的意义。例如,从接受美学看,对于文学文本中的“空白点”“结构缺省”“召唤结构”等,需要译者参与对这些“义—意”形态的充实或重构。这一切都需要译者主体调动自己的各种认知思维能力,参与这些“义—意”形态的建构,只有充分识解这些隐含的或缺省的“义—意”形态,才能进入译文的编码维度或表达阶段。孙艺风(2004:111)在论述翻译的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时认为,理解是阐释的开始,阐释是理解的深入,二者具有雅各布森(Jakobson)所论的“语内翻译”特点。译者不仅需要对原文做出理解,还需要对译文生成过程做出阐释,这就是“双重阐释”或“二度阐释”。由开始理解到*后表达,译者有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理解不足或误解、曲解原意,有意识地通过深入阐释而自我纠正原先的理解。实质上,这就是译者在由理解到表达过程中经历的一种自证行为。孙艺风以对某论文摘要中的“理解是表达的前提和开端”进行英译时出现的理解和用词不当问题为例进行了说明,该英译为“Comprehens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nd beginning of expression”:若孤立看,“前提”和“开端”的英译文无懈可击,但在英译文语境中,beginning of expression造成歧义:①这个短语似乎是表达过程的开始,又似乎是表达过程开始之前;②源语里“开端”不是与“前提”相提并论了吗?不然便是表达开始后(无论在开端的何处)才谈到理解?他建议译为:Comprehens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and antedates (predates) expression,这就是自证的互证行为:一方面证明他者的不当之处或误译,说明成因;另一方面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词择义,从语义逻辑角度做出有理据的阐释,以证明自己译文的语境适切性。
这种现象说明翻译过程中认知逻辑导向的作用,由于双语的语言概念及表达的差异性、多义性、歧义性、模糊性、多变性、语境依赖性,译者主体必须对自己选词择句的主客观性做出有理有据的自证或他证,即对“义—意”形态识解与表达的确证。译者一般都会经历一种证明自己的某种理解是正确或不正确的,或证明他者的某种理解是正确或不正确的过程。确证主义观认为,要确证一个事物就必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而主观和客观的确证都需要知识(陈嘉明,2003:90)。当代西方知识论中产生了证据主义(evidentialism),明确主张确证完全取决于证据,认为某一信念在认识上的确证是由认识者有关该信念的证据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代表人物是齐硕姆(Chisholm)、费德曼(Federman)等(陈嘉明,2003:222)。确证主义观对认知翻译过程研究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对多种译本的译文评价,更需要主客观理据的确证。如上文引用的实例就要求译者对选词择义具有敏锐的逻辑关系辨析之认知思维能力。
翻译理解与表达的确证过程是译者主体认知思维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也是调动各种相关理论和经验结构知识互动互参的认识过程。只有通过积极的认知思维,运用各种潜在的交叉学科理论知识,充分把握了文本“义—意”形态并经过验证或确证后,才能进入译文“编码”或“表达”阶段。故“解码—自证/他证—编码”结构链模式基本上涵盖了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各种认知思维或心智活动,翻译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都体现在这一结构链中。
基于此种认识,本书提出一种新的论断(hypothesis),即译者对语言文化翻译理解与表达的自证与他证能力高低取决于他/她对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生活体验感受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语言反映生活但并不直接摹写生活这一关系的认知度。译者若要正确理解与表达原文语言蕴含的“义—意”形态,必须在认知思维活动中通过各种手段还原语言所描写的形态各异的社会生活场景,感受和理解各类人物内心活动的不同特质、体会人物内心情感及人物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再现自然景物所激发的共鸣等,然后验证语言符号解码与编码的各种内在逻辑联系,在此基础上再参与语境化意义(contextualized meaning)的重构。由此而生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理解语言就是理解生活、理解语言的意义就是体验感受人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曲折跌宕、艰难困苦、快意幸福等的生活经历;翻译理解与表达的过程就是基于对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生百态所体验的“义—意”的建构过程。这些体验形态包括社会体验、自然体验、人生体验、形象体验、情感体验、感官体验(味觉、触觉、嗅觉、视觉、听觉)、经验体验、时空间体验、关系体验、心智体验、角色体验、文化体验、视角变换体验等多向度思维视角的综合运用。这就是笔者在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提出“‘义—意’体验与建构融通式”创新模式的体认语言学基础,该模式也是认知翻译过程研究核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翻译理论只有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才能深入剖析翻译活动的变化规律,揭示实践主体对改造客体的价值取向中的原则认识或对策方法,并由经验感性认识上升为普遍理性认识,再上升到实践理性认识。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宗旨和理论研究目标。
为了深化和拓展翻译研究的维度和广度,本书奉行问题导向原则,将各种翻译难点与重点问题作为翻译过程认知思维研究的重点,讨论的典型实例都旨在揭示复杂的文本特征,如语言的多义性、不定性、不自足性、模糊性、歧义性、变异性、隐晦性、隐喻性、间接性、缺省性、语境制约性、召唤结构、建构性、连贯性、衔接性、互文性、陌生化、风格适切性等(曾利沙,2014a:192)。在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本书突出宏观—中观—微观互通的原则,将义素—字词—短语—小句—语段—语篇—语境—社会—生活体验—文化体验—思维体验等语言与非语言层面的各种难点问题纳入翻译认知思维机制研究中。在方法论上,本书强化了对翻译难点重点问题解决对策的程序化、推演化、理据化、形象化、可视化解析过程,如给有些译例配上反映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的图片,或以图解的方式程序性地描述思维推论的可操作性过程。这种可直观的研究方法强化了对翻译活动本质特征的认识,深化了对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区别与联系的认识,并从思维运作理据层面对翻译活动过程的认识提供了一系列可分析、可描述、可阐释、可推论、可印证的基本概念知识,如定义、外延、内涵、前提、预设、蕴涵、含意、种属、命题、范畴、属性、推论,以及形象、情感特质、意象、意境、人物性格、关系、情节、矛盾冲突、艺术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再创等,将其融入典型案例的翻译理解(解码)与表达(编码)过程中。
本书共十三章,第一章为导论,导论对本书的研究背景与主要思路等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二章讨论认知思维与翻译过程研究的概念辨析,主要任务是对核心或关键概念做出科学界定。主要观点是理论研究必须对概念做出明晰的外延和内涵界定,概念内涵不明必然导致概念的规定职能不明。本章将认知过程界定为“一种由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思维形式和方式联动运作的意识活动过程”,其思维运作包括感觉、知觉、辨认、联想、分析、推导、判断、印证、析取、抽象、分类、概括、综合等,并阐发了“研”与“究”的内涵特征与创新之道。
第三章阐述翻译过程“义—意”体认与建构研究的哲学基础。一门学科理论的发展必须具有科学基础,尤其是哲学基础。其主要观点是认知翻译研究应从哲学高度去领会或把握认知视角下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系统方法,不宜局限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维度。本章从多维视角论述了认知翻译活动关涉的“义—意”识解与表达过程研究的主客观互动的哲学依据,并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描述。
第四章论述翻译过程“义—意”体认识解与建构的认知机制。主要观点是认知翻译学宏观理论研究目标、要求、对象、任务、方法等必须与微观翻译实践紧密结合,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不同的体认形态在翻译认知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研究者应坚持由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