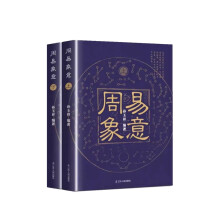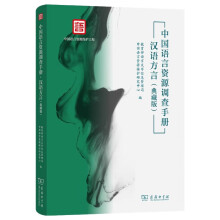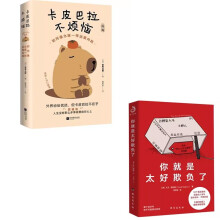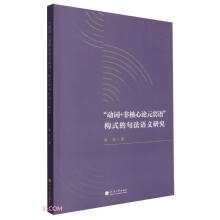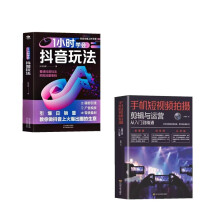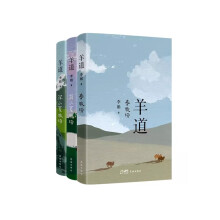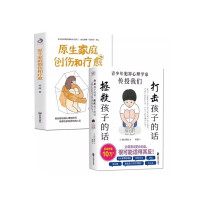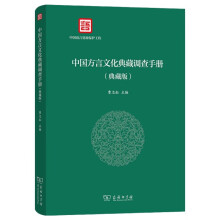第1章绪论
词汇语义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渐从狭义研究范畴走向广义研究范畴。就词汇本身的词典释义讨论词汇,很难实现词汇意义研究的价值,因为其真正价值实际存在于动态的语言使用中,而非静态的、孤立的词汇中。词汇语义离不开词汇所在结构的形式研究,离不开词汇发生的语境研究,离不开词汇与其他词汇之间关系的研究等。正因如此,笔者在关注到典型的词汇语义关系—反义关系时,发现反义词的典型特点之一是经常共现于几类构式中,且英汉语反义词共现构式表现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具有差异,从不同类反义词的概念层面进行共现构式对比,发现同一语种内不同概念反义词的表现也具有深入探究的空间,对语言的深层次问题具有揭示意义。本章首先对本书涉及的关键词进行概述,以呈现出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系,说明本书选题依据,然后提出拟解决的问题,指明方法和路线,厘清研究思路,阐明研究意义,*后介绍本书的框架结构。
1.1关键词概述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反义关系、共现构式、英汉认知对比,因此有必要在此首先对三个概念做简要概述和界定,以初步呈现研究的基础和各关键词之间的关系,为后续各个章节的推进做好铺垫。
1.1.1反义关系
反义关系的概念是在词汇语义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词汇语义学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对反义词概念理解的背景及发展动因,同时也是将反义词置于构式中进行研究的背景和动因。根据Paradis(2013)梳理的内容,西方对词汇意义(wordmeaning)的讨论起源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而词汇语义学(lexicalsemantics)则作为一门学科分支在19世纪开始发展。在开始受关注的初期,因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以及人类文化根源的主要兴趣所在,词汇语义学也就具有历史-哲学倾向,内容涉及的是词源(etymology)和意义随时间发展而形成的分类。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词汇意义主要被视为心理实体(mental entity),意义的变化是心理发展过程的结果(Geeraerts,2010)。到了20世纪,随着与Saussure(1959)相关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兴起,研究者对语言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根本性的认识改变。同时,以往历时研究的思路也发生改变,研究者开始关注共时语言。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是自主的系统,词汇之间在词汇场(lexical field)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关系。词汇意义不是心理单位,而是以“不是 ”的方式来定义。比如,long以其与short的关系来获得意义,换言之,long因为不是short而意为long。结构主义流派对词汇关系*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区分了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如果不同词汇可以填充表达式中同一个位置槽(slot),那么它们之间就是纵聚合关系。例如,“你的书很多”“你的书很少”两句话中,“多”和“少”作为反义词对,具有纵聚合关系。再如,“这儿很冷”“这儿很凉”两句话中,“冷”和“凉”作为近义词对,同样具有纵聚合关系。横组合关系是句子中的线性关系(linear relation),词汇意义是由其在语言使用中前后共现的“同伴”(company)决定的。正因如此,横组合关系的意义研究方法开启了以使用为基础(usage-based)的意义研究时代,即意义描写中语境因素以及语言的实际使用才是主要研究目标,而不是为了研究而创造的语言,反义词的使用可以形成强烈对比效果,可以揭露事物的矛盾或者表达复杂的心理(谢军,1999)。然而,20世纪末,结构主义下的词汇关系观点也开始受到质疑,语言系统不仅仅是词汇关系构成的,还与人的思维以及大脑中的概念结构息息相关,毕竟,语言同时也是心智和心理现象。随之,词汇语义的两大概念研究方法逐渐兴起,一是生成的方法,二是认知的方法。前者是以逻辑形式主义(logical formalism)的方法解构词汇意义;后者则是将人的因素、概念结构和社会框架等都考虑在内,以人们的百科知识为背景做出释义。
随着研究者对词汇语义的深入探究,词汇语义关系的地位逐渐彰显。词汇语义关系主要存在三类情况:同形异义词,如多义词;同义异形词,如近义词;不同形不同义却具有语义关系的词,如反义词。其中,反义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反义关系对组织和限制词汇语义来说至关重要(Lyons,1977;Cruse,1986;Fellbaum,1998;Willners,2001;Murphy,2003;Paradisetal.,2009),甚至是词汇语义关系的原型(Murphy,2003:169)。反义关系的形成基于对比,对比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能力(Willners&Paradis,2010:15),在这一思维能力的作用下,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必然会成为常态,即矛盾法则,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刘敬东和张玲玲,2017)。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思想,源于道家,延续至今。西方反义关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亚里士多德命题对立和范畴划分思想的影响(Lloyd,1966;Apostle,1980),他所创建的逻辑方阵成为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反义关系研究的逻辑和术语基础(Jonesetal.,2012),例如矛盾的(contradictory)和相反的(contrary)。
反义词是指两个词之间形成双向识解(binaryconstrual)的对立(opposition)关系,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位于同一个概念维度,但又具有*大程度的差异,因为它们表达的是同一语义维度上截然相反的两个语义特征(Paradis&Willners,2011)。例如,tall和short是形容高度的一对反义词,是纵向延展维度上的语义关系,可以用来形容身高或物体高度,而long和short则是在水平延展维度上的语义关系,可以用来形容物体的长度。反义关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语篇语境中的不同表达目的。因此,研究者指出,反义关系词的特殊性在于两个词语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而不是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一定限定于同一语义域(Paradis et al.,2009;Paradis&Willners,2011)。随着词汇语义学的发展,反义词的本质也得到了逐渐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初受结构主义流派影响,反义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词汇之间的纵聚合关系,随着词汇语义概念层面的揭示,尤其是随着以使用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兴起,反义词的横组合关系之于理解反义关系的意义受到关注,词汇关系的本质也受到质疑:为什么有些反义词倾向于共现,其动因是什么?反义词的反义关系有无程度差别,有何表现?诸如以上各类相关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反义词所呈现的是概念联系,而非简单的词汇关系。
本书以构成反义关系的词汇所共现的语言表达式为载体,探究反义词共现的动因。这一思路便是沿承词汇语义关系研究的思路和现状,以其概念关系的本质为切入点,探究概念层面的关系在句子层面的互动及影响因素,以期贡献于反义关系的横组合特点。
1.1.2共现构式
正如上节所述,“共现”(co-occurrence)意为共同出现在同一表达式,是组合关系的表现,主要是相对于在同一句法位置可以相互替代的纵聚合关系提出的。聚合关系,是人们在语言编码过程中,对客观现实的范畴化和再范畴化过程(Lakoff,1987),是一种选择关系,非此即彼,而组合关系则更多地体现语篇衔接,为语篇附加必要的信息(Cruse,1986)。那么,如何去解释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这两类看似不相容的关系本质同时集中于一种语义关系呢?Murphy(2003)提出,反义词之间的规约性关系实际上是它们元语言知识的一部分,元语言知识又引起了它们的共现。Murphy(2006)继而提出,反义词对构成了一类固定构式,使其语义上的聚合关系在组合关系中得以实现。Langacker(2008)从认知语法的角度论述了两类关系的概念本质,也为其共存于反义词对提供了理据:聚合关系属于范畴化关系,是图式与各个例证之间的关系,是构式外的关系;组合关系是部分与整合结构之间形成的具有连贯性的组合,语义上,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都是有概念重合的,这是其整合的基础,组合关系是构式内关系。两种关系的性质在本质上都是概念化的,所以必然有其共存的概念基础。
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在以词汇关系为基础的研究中发现,反义形容词的词汇关系是通过两词共现于同一个句子而不是在同一句法环境中相互替代实现的(Charles&Miller,1989)。还有研究者对语料库考察发现,相对于近义词来说,反义词共现的概率远远高于偶发概率(Justeson&Katz,1991;Jonesetal.,2012)。根据对语料的整理和分析,研究者有两大发现:一是反义词往往高频共现于某些特定结构;二是反义词共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语篇功能(Jones,2002),正如Cruse(1986)提出的,横组合关系可以更大程度地体现语篇衔接,为语篇附加一定的必要信息。对英语中反义词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应用于其他语种、不同语域等,尽管具体功能和结构因文化差异等因素有所区别,但皆论证了以上两大发现。随着更多研究方法提供的证据积累,如心理学实验、神经学实验等,共现研究中所揭示的反义关系的本质实为概念联系,而非词汇关系。同时,共现研究也揭示了反义关系具有典型程度的差异,在某一语义域内,有的反义词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共现频率高,且可以不依赖语境,而有的反义词之间却需要更多的语境信息支撑,才能实现反义关系。因此,反义词共现现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主题,其意义不应该仅仅限于已有发现,其他相关方面如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共现结构和语篇功能的差异等,也值得关注。
构式研究存在几大流派,本书采用的是Goldberg(1995,2006)构式语法理论中的构式。该理论强调形式和意义的匹配,意义不是表达式各成分的简单语义相加,而是存在无法从形式中推导出来的意义内容。以往各语种的研究结果表明,反义词所共现的结构往往比较固定,说明形式和反义词共现现象之间应该具有内在联系,某些形式倾向于容纳反义词,而某些形式不容易接受反义词进入;相反,反义词的关系特点使得有些反义词被吸引进入某些形式结构,更好地发挥反义关系的功能,而有些反义词则与某些形式相排斥,无法实现其关系的显化。既然反义关系是一种概念联系,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反义词之间的概念语义层面,其次还需要考虑概念语义如何与其所进入的结构相互融合。本书将这类接受反义关系词共现的结构看作是共现构式,从形式和意义匹配的角度探究反义关系的句法和语义表现。
1.1.3英汉认知对比
英语中反义关系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体现在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指向相同的研究成果。汉语反义关系研究相对薄弱: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对反义关系的纵聚合关系的分析上,对反义词共现现象的关注较晚;另一方面,汉语的语言现象更加复杂,从形式上寻找反义词的规律性共现构式具有一定难度。尽管如此,反义词共现构式仍然具有英汉对比的必要性,毕竟反义关系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认知系统,还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大部分,也许是所有的语言系统,所以,反义词的语言对比研究是必然趋势,也是揭示反义关系本质的重要途径,即不同语言中的反义词使用情况可以从不同角度贡献于反义关系的研究。
如前文所述,反义关系是一种概念联系,对此,认知语言学提供了较为细致的概念层面的分析方法,尤其是认知语法的方法。反义关系具有程度上的差异,并且受到语境的影响,因此动态识解这一双向关系有利于捕捉其本质特征。更重要的是,英汉对比下的异同之处,仍要以人类的基本认知能力为基准进行判断、区分和分析,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反义关系作为概念关系的本质。
经过以上对反义词、共现构式、英汉认知对比的解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通过英汉反义词共现于同一构式的语言现象的对比研究,从认知角度解释反义关系的跨语言表现异同的原因。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