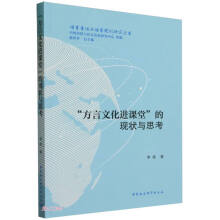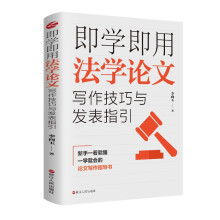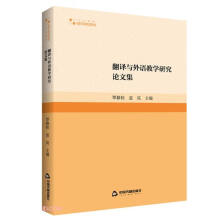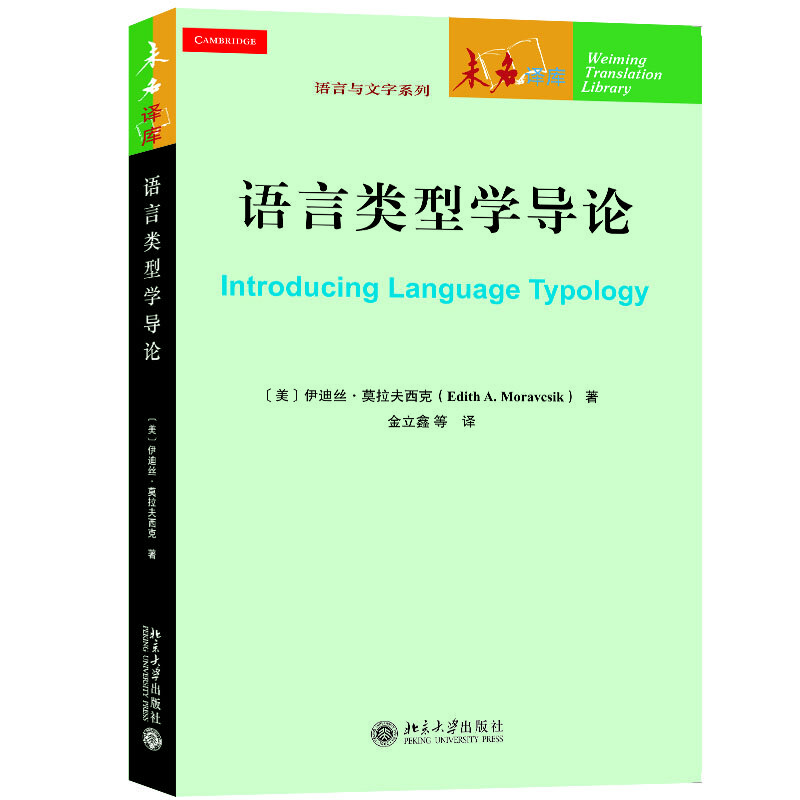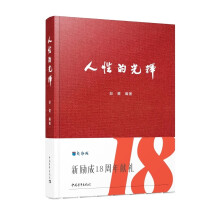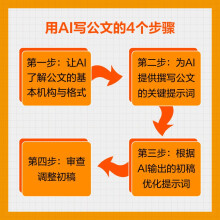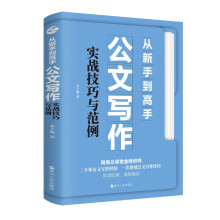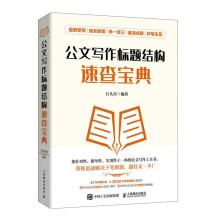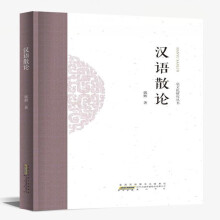绪章 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
第一节 语言与语种、人类与族群、语种与族群
“语言”的形成与“语种”的形成密不可分;人类的出现与族群的产生密不可分;语种的形成与族群的形成亦密不可分。这些密不可分的对象及其关系就构成了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广阔而坚实的背景基础。
一、语言的形成与语种的形成
(一)“语言”与“语种”的概念
语言的形成与语种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是人类的生物机能,凡是人都具有语言,就是指这种生物机能。语种则是人类某一群体(族群)之内的交流与认知工具。即是说,语言与人类是一对相对概念,语种与族群是一对相对概念。语言是指全人类的生物机能,语种是指某一族群所操的语言、所具有的生物机能。语言与语种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二)语言由人类“交际”“认知”动力驱动而产生、演化;“语种”与“群体”的边界
1. 语言产生的“交际”“认知”动力
语言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从距今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的产生、演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语言也不是突然就出现的。根据考古学界对人类发音器官进化的研究、推测,语言在距今约5万年时产生。这是语言产生的断代,是人类具有语言这一生物机能的断代。
如果这一推论能成立,语言的产生要比“人”的产生晚得多,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类起源于远古非洲原始部落的一对男女,语言不会随着这一对滋生出“人类”的“人”产生。
语言的产生,是出于人类群体之内“交际”的动力需要,不管是日常居住生活,还是生产劳动[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创造(铸造、锻造)工具],可以说,语言是在“人类”群体的交际推动中滋生、演化的。这是作为生物机能的语言产生的外在动因。语言的产生除了“交际”这一外部动力以外,还有“认知”这一内在动因,语言也是人类认知的产物。
2. “语种”与“群体”的边界
“语种”是在不同“群体”之内在“交际”“认知”动力推动下滋生、演化的。“群体”的边界就是“语种”的边界,“群体”的四维时空边界就是“语种”的四维时空边界。语种边界之内是交流、认同(认知的同一性形成语种世界观),语种边界之外是隔膜/非认同,语种边界就是这一语种与那一语种之间的分界线。
要指出一点,德国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实际上是指“语种世界观”,即某一族群所操语种对世界的认知、态度等语种意识形态,这是较之于哲学、政治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据此,意识形态可以区分为两类,如图0-1所示。
图0-1 意识形态分类图
非语种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语种意识形态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非语种意识形态是在语种意识形态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语种世界观与非语种世界观滋生出“群体的边界”,进而滋生出“国家边界”,国家边界可以区分为两类,如图0-2所示。
图0-2 国家边界分类图
地理边界一旦确定,就会形成明晰的界限,可以称之为“硬边界”(硬边疆)。但是语种(举语种以赅文化等)的边界一方面有明晰的一面,这是俄国数学家康托尔的经典集合论所讲的;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美国数学家扎德的模糊集合论中边界不分明的提法,两种语种的分界线之间会有一个交汇地带,会有一段模糊区域,这段模糊区域就是两个“族群”、两个“语种”的接触、交混、融合区域。非地理边界可以被称为“软边界”(软边疆),软实力就是软边疆,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就是“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软边疆(相对于英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软边疆)。“半月形地带”是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传统软边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半月形地带”这一传统软边疆将会有一个开放性的演进(通过国家通语的传承、传播而演进)。
(三)语种随族群而产生,族群随语种而出现,语种与族群在产生上互为因果
语种的产生要比语言的产生晚得多。从源头上讲,语种是语言的裂变与分化,语言随群体的“分化”而产生新语种。当然语种也会因群体接触、交混、融合而产生新语种,其前提就是至少有两种语种的存在而且二者之间有接触、交混、融合。没有这一条件,因接触而产生新语种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语言裂变与分化在先,语种接触、交混、融合在后,可以说,先有语言后有语种,如此说,语言这种生物机能就成为人类所有语种的“祖语”,现存7 000(语种的区分是一个难题,因为语种的标准难以确定,全世界的语种永远不会有确切的数字,这里的语种数据是依据美国人的提法得出)多种语种,就是祖语“语言”的后裔、分支,就是语言的“语种”。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与认知工具,语种是随着人类群体的分化、演化而产生的,“群体”分化、演化为“族群”,“语言”就会随群体分化、演化为“语种”。语种与族群共存亡。语种会因族群而滋生、存在,也会因族群消亡而消亡。匈奴称雄于西汉,随着匈奴族群的消亡(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于中亚,此时匈奴作为一个族群已消亡),匈奴语作为语种也荡然无存,仅仅留下《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中用汉字记录(把汉字作为记音工具,类似于今天用国际音标记音)的278个词语,其中绝大多数是“专有名词或称号” 。族群会因语种的滋生、存在而滋生、存在,也会因语种的消亡而消亡。要指出一点,有时候语种消亡,族群并不会因之而消亡,但是该族群的语种属性就不存在了。这表明,语种是族群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四)语言与语种的断代
1. 语言的断代及其断代理据—语言与绘画同源
语言的断代问题上文已经提及,这里略作补充。关于语言的形成时间,依据考古学界的看法,大致形成于距今约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语言形成的断代依据,不是来自语言资料自身,因为谁都没有见到过距今约5万年的语言资料(有声资料或文字资料),其断代依据主要是来自发音器官的进化与形成。人类的发音器官的构成标准是什么?今天人类拥有的发音器官已经是成形的发音器官,但是在成形的发音器官之前,尚存在一个前成形器官阶段。该问题难度极大,留待以后另文讨论,此不赘。
绘画与文字同源,其实,绘画与语言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如果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来看,语言的形成断代可以定在旧石器时代距今5万—2.7万年。笔者提出的这一断代看法,是基于艺术与语言同出一源的道理。
根据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对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分类、分派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与语言的同构关系。首先,艺术与语言都是认知与表现;其次,艺术与语言统一于符号,语言是以声音为符号来表示意义,艺术是以线条为符号来表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都属于“二维符号”。
从图0-3可以看出,语言就是对声音赋值以意义构成的,绘画就是对线条赋值以意义构成的,没有意义的语言、绘画是不存在的。
图0-3 语言与绘画表达式映射图
如果站在形式的角度看,语言、绘画具有形式同构性。线条本质上是一维的,在旧石器时代人手中,一维线条变成二维屈折(曲折)以表意,产生了表意的二维性(形象、寓意);语音本质上也是线性的,在人类口中,断断续续产生了分节的音象(音象、寓意)。这是“绘画符号”(艺术符号)与“语言符号”同构同源的内在理据。可以说,给绘画符号赋值以语音就是语言符号,纳西族东巴文就具有这种属性;同样地,给语言符号赋值以线条即是绘画,“插画”就具有这种属性,古代文人往往兼善诗画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说“词是一件艺术品”,因为词与艺术都是直觉的产物;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美学就是语言学,因为审美与语言都以直觉为基础,都是直觉的产物。萨丕尔与克罗齐都观察到了艺术与语言的深层是同出一源,即艺术基因与语言基因具有形式上的同构性。
裴文中所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约在距今2.7万年以前。裴文中说:“艺术的起原,并不在历史时代,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之初,若按现在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的年来计算,约在二万五千年以前。” 依据艺术与语言同出一源的道理,可以依据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来给语言的起源断代。
依据裴文中对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断代(距今2.7万年以前),结合上文考古学界关于语言产生于距今约5万年的说法,据此,语言产生的断代可以定在距今5万—2.7万年,即语言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产物。
此外,声乐在起源上与语言也同出一源,不过声乐的起源与超音段几何空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语言的起源与音段空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这个问题拟另文讨论,此不赘。
2. 语种的断代
语种的断代可以根据相应族群的代际标准来判断 。语种与某一具体族群在形成初始总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