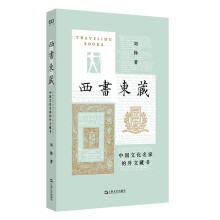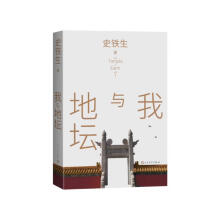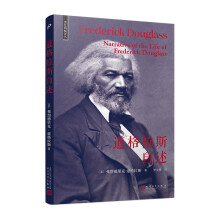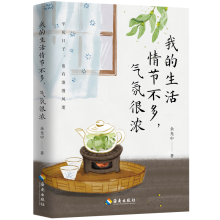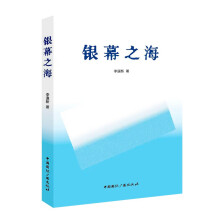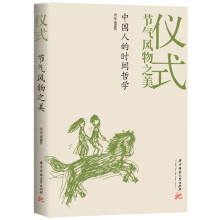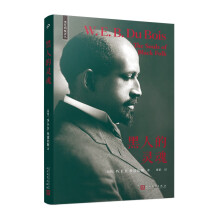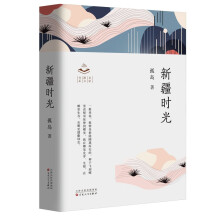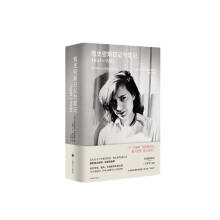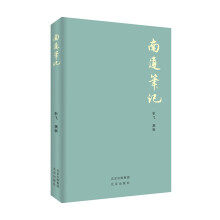信仰的背离
我出生时,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信上帝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何要信;他们的前辈和长辈们倒是信上帝的——不过,他们却不知道为何要不信上帝。然而,人们总是喜欢在感觉的驱使下,而非在经过理性思考后做出判断——此乃人心使然。因此,在这些不信上帝的年轻人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以人欲来替代上帝。不过,我却偏偏是那种总是游走在自己这个圈子边缘的人。我不光看到圈内有不少志同道合者,我还看到,在这个圈子外围还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因此,我这才没有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抛弃了上帝,此外,我的心中从来都没有给人欲留下过一席之地。在我看来,上帝或许显得不接地气,但却是可能存在的,因此,人们应当敬拜他。反观人欲,它充其量只是个生物学概念,顶多告诉我们,我们是人类。人欲根本就不值得人类敬拜,人如果要敬拜它,还不如去敬拜别的动物。敬拜人欲就意味着要礼遇自由与平等,这种信仰总是会令我大惊失色。这就好比那些把动物视为神祇,或是神祇都长着动物头的古代教派,又借尸还魂了。
于是,既然不知道如何去信仰上帝,也无意去信仰形形色色的动物(神祇),我便和圈子边缘的其他人一道,与各类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一般把这种疏远叫作堕落。堕落即彻底的麻木不仁,它才是生命的底色。倘若堕落也能思考,心脏就不用跳动了。
那么,对极个别像我这样浑浑噩噩度日、不知道该如何活着的人来说,抛开被我们放弃的生活方式、被我们思考过的命运不谈,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中究竟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无从得知,为宗教而活是什么样的,因为理性无法理解信仰;我们也无意去信仰人(欲)这一抽象概念,甚至都无法对这一概念做出回应;我们之所以还算是个人,完全是因为我们对生命还有点儿美学意义上的思考。我们对大千世界的肃然安之若素,对上帝的神性无动于衷,对人类的本性不屑一顾;我们百无聊赖地被盲目的感觉牵着鼻子走,以一种精致的享乐主义耕耘着生命之田,只是为了取悦自己的脑神经。
我们只记住了最基本的科学准则——万物终究摆脱不了各种致命的法则,可我们却偏偏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应对这些法则,因为它们决定着应对的结果——我们还知道,这一准则如何酷似那更加古老的万物宿命论这一神性法则。于是,我们便放弃了一切努力,就像铁了心不想当运动员的身体羸弱者,我们这才如同一个对感觉充满疑虑的学者,俯身研读起了感觉之书。
我们拿什么都不当回事,认为感觉才是我们唯一可以当真的现实,我们一头扎入感觉的天地,像发现了未知的疆域一样在其中游走探寻。如果我们不仅孜孜以求美学上的沉思,同时还煞费苦心地想披露这一沉思的方法与结果,那是因为我们写下了那样的诗或散文我们之所以写它们,并不是想改变别人的意志,也无意去影响他人的理解——我们其实就像是朗读者,想通过大声朗读将阅读这一愉悦的主观感受彻底地表达出来,使之成为一个客观事实。 我们都很清楚,每一件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不完美的,而我们最拿捏不准的美学沉思对象莫过于我们所写的文章了。但是,话说回来,万物都是不完美的。落日没有最美的,因为总会发现更美的;轻柔拂过的微风纵然再能令人安然入睡,也总会有比它更能让人酣睡的。于是,无论是(喜欢)对着雕像还是对着群山沉思,我们都既热爱书本又留恋过去的日子,都会梦见一切事物,并把它们化为己物。梦醒之后,我们还会写下描述与分析梦境的文章,好让梦境成为我们可以把玩的身外之物,就好比它们是某天发生过的真事一样。
悲观如维尼者,可没有这样的心境。在维尼看来,活着无异于坐牢,他在生活的牢笼中只好编编草绳,如此方能在不停的劳动中忘却尘世。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意味着要悲观地看待万事万物,这种态度既显得过分也让人不适。尽管我们的确认为自己创作的作品没有价值,但我们创作它也的确是为了让自己不停地劳作,不过,我们可和那个在牢笼中忙于编草绳,好忘却自己命运的囚徒不一样;我们倒是像一个在枕头上绣花的姑娘,纯粹是为了让自己不要闲下来。
P2-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