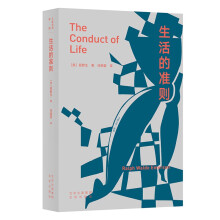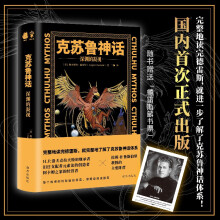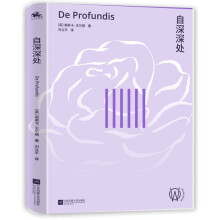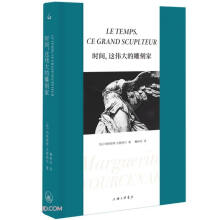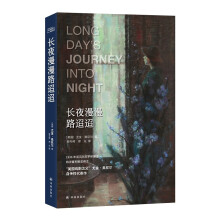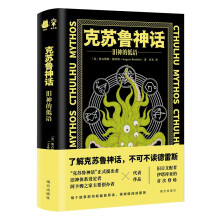19 世纪女作家对同时代的人来说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作家。一个女小说家如果不用男性笔名伪装,必料定评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女性身份上,并把她与当时的其他女作家归为一类,无论她们的题材和风格有多大的不同。个人的成就总会被放在相形见绌的刻板组合之中,这样的认识始终刺激着女性小说家。乔治·爱略特反对有人把她比作黛娜·马洛克;夏洛特·勃朗特推迟发表《维莱特》(Villette),为的是可以不同盖斯凯尔夫人的《露丝》被放在一起评论。勃朗特尤其希望阻止男性文学权势把女作家变成争夺同一块小地盘的竞争者和对手。“妒忌是作家的本性”,她给盖斯凯尔夫人的信中写道,但是“我们就是不听他们的;他们不可以把我们变成敌人”。
我们往往忘记了,维多利亚书评人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女性当成靶子,在批评文中对她们进行人身攻击。戈登·海特(Gordon S.Haight)在《乔治·爱略特批评百年》中所犯的一个错误可说明现代人这一普遍的盲点。海特引用 E.S.达拉斯(E. S. Dallas)评爱略特的话,后者说她作为散文作家没有什么“英国人”(Englishman)可以企及。达拉斯实际上用的词是“英国女人”(Englishwoman)。对于海特来说,这样一种区分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于乔治·爱略特则不然。自19世纪初以来,绅士派头的评论者就一直对女小说家抱着屈尊俯就的态度。例如,1834 年,《弗雷泽杂志》(Fraser’s)的评论人幸灾乐祸却过于草率地认定了《拉克伦特城堡》(Castle Rackrent)和《在外地主》(The Absentee)的所谓真正作者:“对了,这正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埃奇沃思小姐根本没有写过这些埃奇沃思小说……所有这些,正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所怀疑的,都是她父亲的作品。”然而,批评中高度集中关注女作家正当领域的论调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出现。维多利亚批评家用尽聪明才智,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来微妙地强调女性的特殊性,而避免使用“女作家”(woman writer)这个职业上中性的称呼。这些词汇有女作者(authoress),女子的笔(female pen),淑女小说家(lady novelist),甚至到了1897 年,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出版纪念文集《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女小说家》(Women Novelists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时,还在文绉绉地说,由“健在的深谙本行技艺的女性行家里手”(living mistresses of the craft)描述的“女士长篇小说家”(lady fictionists)。整个五六十年代,对女小说家的理论批评和具体批评数量激增。几乎没有一份报刊不发表文章谈女性文学,几乎没有一个批评家不对女性文学特有的和潜在的品质发表意见。
这很像20世纪60 年代后期的情形,女人写的和写女人的文学市场有了很大的扩展。19 世纪50—60年代的形势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正在应对一种看来具有革命性、并在许多方面颇具威胁性的现象。这个时期女性写的有影响力的小说数量一直在上升,故男性报人被迫承认女性在小说创作方面正在胜出,不仅在英国如此,在欧洲和美国亦然。情况变得很明显了,简·奥斯丁和玛丽亚·埃奇沃思不是什么失常怪人,而是女性参与小说发展的先驱人物,这时再开什么跳舞的狗之类的玩笑似乎已不足以作为回应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