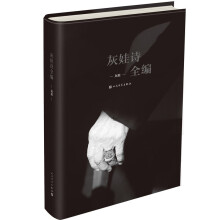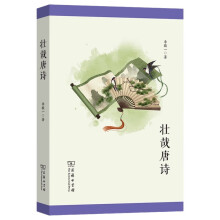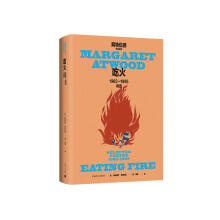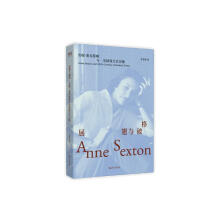第一辑
花蹦蹦
——给刀刀
今天下午,一只小昆虫
爬到了你们班来来的胳膊上:
黑色,满是小白点,长长的细腿。
来来尖叫了起来,小朋友们拥过来
帮她把虫子掸到了地上。
一些小朋友说是大蚊子,另一些说是
跳蚤,他们都认为它会咬人
决定乱脚踩死它。
只有你
从小跟着我认花识虫的
小小博物学家,三岁时就认得
它是斑衣蜡蝉小龄若虫,俗称
花蹦蹦,只吸树汁,不咬人。
你告诉小朋友们它是对人无害的花蹦蹦,
你试图阻止他们疯狂的踩踏,但
没有人相信你。个别人只知道
斑衣蜡蝉的大龄若虫是红黑相间
不认得它小龄的形态,更加指责你
胡说八道。没有人理会你。
小朋友们继续嘉年华一般地踩踏着花蹦蹦。
你在旁边哭着,一遍一遍地高喊:
“它很可爱!它不会咬人的!”
花蹦蹦被踩得稀巴烂的那一刻,
你突然失控了,跺着脚,发出
刺耳的尖叫,用尽全力嘶吼着说:
“它也是有生命的呀!”然后
你哭着扑向所有人,
手抓,脚踢,怒目相向,
被老师摁住了很久都不能平静。
老师向我讲述这件事时,重点是
让我教你如何控制情绪。
我听到的却是你被迫成长时
幼小的骨头里传出的愤怒的声响:
女儿,这或许是你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是群氓的碾压和学识的孤绝,
什么是百无一用的热血,
尽管我真希望你一辈子
都对此毫无察觉。
2018/06
埃库勒斯塔
1
埃库勒斯塔,公元二世纪
罗马人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的海边
留下来的灯塔,是另一片
闭锁在石头里的海。在塔里
能听见海水的手掌击打着
石块的内壁,你附耳过去,
就会有一小滴被囚禁的海
挣脱了物理学的诅咒,溅到
你的眼中。当你登上塔顶,看见
腋下夹着大半个天空的大西洋
从远处呼啸而来,丝毫感觉不到
你眼中有细小的急切之物
纵身跳进了塔下的巨浪。
你或许能听见石头深处传来
海水的鼓掌声,像一群狱中志士
在庆贺又一滴狱友重返骄傲的蓝。
2
我登上埃库勒斯塔是在
十月里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
城市、原野、礁石
在大海面前相互推搡,轻易地
把视野让给了一个巨型的远方。
塔顶有三三两两的白人观光客,
我能从他们对远方的赞叹里
识别出法语、德语和波兰语。
然后我注意到了站在护栏尽头的
那个孤零零的老人。
他一直在哭。
对着远方,张开嘴,闭着眼哭。
他努力不弄出任何声响,肩背颤动得
像暴风中一副快要散架的农具。
他长着一副东亚面孔,衣着
不似任何一类观光客。我小心翼翼地
用汉语问他是不是中国人,
他点了点头,试图用磨损的衣角
擦去满脸的泪水。我递给他一张纸巾,
慢慢问起他为何独自在这里、
在这个中国游客罕至的地方默默哭泣。
语言不通受了委屈?跟丢了旅行团?
他感激了我的善意,但并没有
替我解谜,只是告诉我,他来自
河南南阳,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他的村庄。
突然间,我想起:埃库勒斯塔就在
去往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上。
我问他:“您是天主教徒,
要徒步去圣地亚哥?”
他那双哭红了的眼睛骤然一亮,
想要说话,却又犹豫了一下,手画十字
朝我礼貌地笑了笑,而后踉踉跄跄地
走下了楼梯。我站在他刚才站过的地方
想看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巨型的远方会幻化出怎样的悲伤?
我看见腋下夹着全部天空的大西洋
从海平线呼啸而来,我猛然感觉到
眼中有海量的急切之物
想要纵身加入塔下无边而骄傲的蓝。
2017/10—2018/01
花灵灵
——给慌慌
这所大学把“谢谢”二字变成了一对耳朵,
这所大学的迟疑因毕业而骤亮成眼睛或者中子星,
这所大学抖了抖白毛上层层覆盖的手形时光,
这所大学尾巴高耸,如同笔直得堪忧的情义,
这所大学脚步轻巧,朝着暮色中的东门一路小跑,
这所大学要去搭乘地铁追赶你,成为你的行李。
这所大学会一直在你身边寻找那只名叫花灵灵的大学。
2018/07/13 写于徒儿慌慌的毕业离校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