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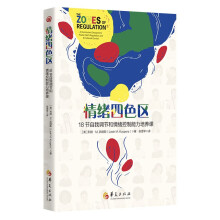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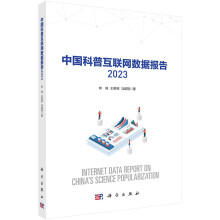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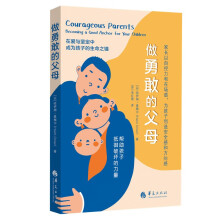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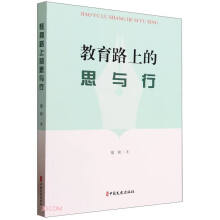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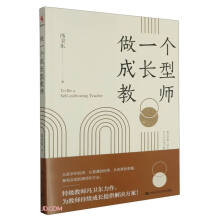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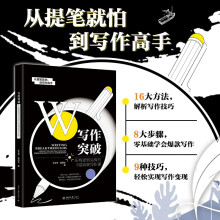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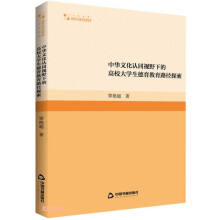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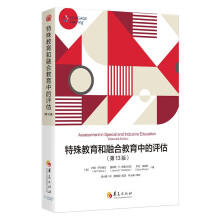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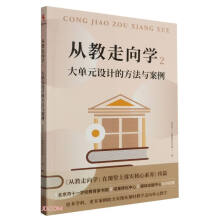
第1章 绪论
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发源地,是现代科研人才的主要培育场。作为科学家成长的摇篮和科研突破的引擎,研究型大学在科学技术进步、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中发挥着愈益突出的作用。充分认识科学技术趋势和人才培养规律,为研究型大学确立与国家及人类命运相一致的战略目标,控制保障每一阶段战略目标逐步达成,是研究型大学战略管理研究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必须正视且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1.1 研究背景及缘起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政府和社会对研究型大学的期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烈而迫切。人们希望研究型大学及其培养的人才能使我们的生活设施更加便捷,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愈发清洁,使我们的生活威胁日益减少,使我们的国家科技更加先进。近年来,“卡脖子”技术问题在我国凸显,政府和社会对研究型大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施战略管理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加速器,而研究型大学真正地实施科学战略管理仍需进行内外突围。
1.1.1 中国强国建设对研究型大学的期待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2017),这取代了原来长期使用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表述;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包括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这些强国目标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各个领域的体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一庄严宣告意味着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和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国现今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强国建设工作不断规划和落实。2021年9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2020年10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形成了其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我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健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教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全新事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肩负的使命更为重大。实现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研究型大学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以下简称“双一流”)首轮建设完成之际,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这是全面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的一个重要文件。该评价办法明确“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突出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克服‘五唯’顽瘴痼疾”,把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目标融合在一起,走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成效评价体系的重要一步,为高校争创世界一流指明了方向。目前,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对高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高校的核心任务,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勇挑重担,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大力加强基础研究,聚焦国家战略,加快科研攻关。“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排头兵,要主动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引导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即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的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产出一流人才、一流学术成果和以社会贡献为目标,科教融合,创新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学科领域,建设全球育人和科研高峰,加快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重大贡献。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和认识到研究型大学在国家与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及巨大作用。近年来,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科教融合、创新发展成为新时代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突出特征。2017年“双一流”建设以来,我国研究型大学围绕国家战略和学术前沿,科研能级和科技创新能力有了长足发展。中国强国建设期望研究型大学适应社会发展步伐,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步伐,引进和借鉴企业经营方略,科学制定、实施发展战略,真正做好战略控制,持续提升大学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强国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发挥特殊功能(陈新忠和李忠云,2006a)。有效的战略控制能保障研究型大学沿着自己制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前进,在系统思考、超前思考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整合校内外力量,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战略目标和使命,实现跨越式发展。
1.1.2 办学体制转变对研究型大学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引发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深度变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各项事业由政府统一管理、经费由政府统一提供、招生由政府统一计划、毕业生由政府统一分配,对于未来长期发展的问题不需要主动考虑(陈新忠和李忠云,2005a)。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于是开始实行三级办学的体制(中央、省、中心城市)。在三级办学体制下,“条块分割”的格局得到不断强化,中央各个主管部门之间(“条条”)、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块块”)、中央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的办学互不相通,培养人才都强调优先满足各自的需求。在实践中,只有中心城市办学真正将高等教育的两级办学转向了三级办学的新格局。然而,中心城市办学即使在投资来源上有了一些变化,仍未能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发生巨大变革,依旧摆脱不了国家办学的“影子”。这一时期,除了地方政府办学积极性得到提高之外,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的尝试也取得了进展。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出现民办高校,但这些民办高校暂时没有获得合法性地位。直到1984年,我国才诞生了首批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海淀走读大学、浙江树人大学、四川天一学院和黄河科技学院(蒋华林,2016)。之后,兴办民办高等学校的浪潮席卷全国。然而,各校办学质量良莠不齐,以至1987~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先后督促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达不到基本办学条件的民办高校进行清理。这一时期,国家尚未出台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的相关政策,民办高等教育一直缓慢发展(皇甫林晓和梁茜,2020)。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于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大,中心城市办学与民办高等教育的萌芽对原有办学体制发起了最早冲击,但是波及范围和冲击效果非常有限。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需要加快高等教育发展。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我国要进行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扩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决策权和包括对中央部门所属学校的统筹权。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从法律上保障了地方政府获得区域高等教育的主导权、决策权和统筹权。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央主管部门集中下放了所属高校,地方政府开始掌握日渐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及地方高等教育的统筹权与管理权,逐渐成为真正独立的利益主体,“块块分割”的格局最终形成并不断得以强化(阙明坤等,2018)。这一时期,民办高等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分别于1999年和2002年先后出台,我国以法律形式对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予以肯定与鼓励。在实践中,伴随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国内相对发达地区的一些公办高校开始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自下而上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针对这种办学模式,国家进行规范管理并将其改名为独立学院。在政策支持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到300多所,成为民办机制下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增长点(阙明坤,2016)。199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该法第四章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法制的健全,政府对高校从直接管理变为以间接调控为主,形成了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学校自主办学为主体的高校运作机制。在新的办学体制下,高校的命运和前途由原来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变为一定程度上由自己把握,最立决策的功能得到强化,促使高校更多地思考自身的未来,实施战略管理,战略控制问题凸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教育领域做出更为深入的变革。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致力于使政府、高校和社会等相关利益群体紧密合作,通过简政放权,更大限度释放市场力量,激发高校办学活力,促进高等教育办学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平衡(张万朋和程钰琳,2017)。这一时期,努力构建政府、市场和高校之间的新型关系,改变高校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成为改革主线。其中,高等教育领域“管办评分离”的目的在于彻底改变政府部门越位全包全管、学校失位无权举办、社会缺位无从参与的传统办学局面,突出学校与社会在国家教育系统中的主体性与自觉性,实现政府、学校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