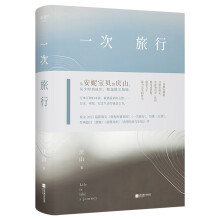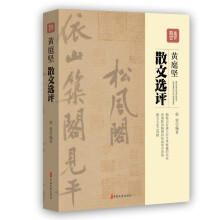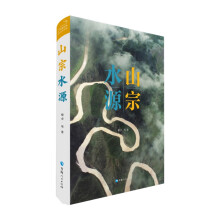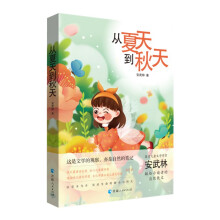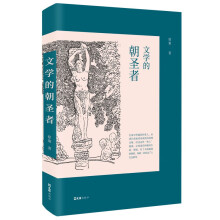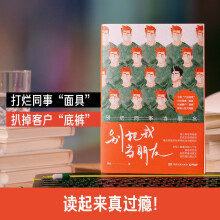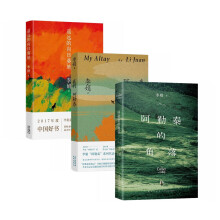盛家坝区公所(1998年改称乡政府)大门的左边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梧桐旁边是一棵桂花树。有人说“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那棵梧桐树上却住着一只神秘而悲苦的大鸟。而那棵桂花树,我们视若珍宝,浇水、施肥,精心呵护。八月丹桂香,摘一小撮掺在茶叶里,再慢慢晾干,异香扑鼻。
夏天晚饭后,我经常站在梧桐树下抽烟,思考人生,直到周围灯光一点点亮起。我在短街上已逛了千百回,熟悉的面孔已看够,想说的话已说完,晚上还有大把时间看书,不发呆能干什么?
人们冬天喜欢群居,夏天更乐于独处。在那个互联网、手机远未普及的年代,夏天日落时分的寂寞潮水般涌向小镇上每一个单身男女,一个不那么温柔的秋波已足以使人沦陷。没有马景涛式的告白,也没有三五年终成眷属的佳话。我曾觉得小镇上的男女之情过于平淡,若干年后才明白,都市男女可能有着更多迷茫。要是在广州,你怎么会知道,街头开店那胖姑娘的爹曾当过村支书,那位和善的大叔其实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叱咤风云?
与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喝酒在盛家坝即使算不上美德,也不被视为恶习。我曾看到一位身居要职的前辈喝醉后歪歪斜斜地拥着州里来检查工作的女领导到文化站跳舞,一长截皮带从裤襻里挣出来呼扇呼扇,大家一笑置之。一个青皮男醉酒后骑着他的破摩托摇摇晃晃挣扎着要回家,围观群众亦步亦趋。车在拐弯的地方冲向坎边,坐垫掉到沟里,围观群众哈哈大笑,直到警察赶来善后。还有位大哥,村里的书记嫁姑娘,他去喝喜酒,喝高了。姑娘出嫁,当爹的舍不得,忍不住落泪,他也跟着呜呜咽咽地哭。当爹的说,姑娘头上戴的花太红太艳太不庄严,必须取下来,他立即表示赞成。好几位年轻老师因善饮而闻名一时,故事婉转曲折。独酌、对饮、欢会,像享受生活,像与人较劲,又像心中确有块垒。
在这里打牌也是不错的消遣。本人也多次捧场,不过浅尝辄止。有好几个深夜,我听到有人敲开同事的门,说是输光了亟须“赶账”(借钱)扳本。有一天夜里,旁边一帮老头儿突然大吵起来,有一位直喊要打人,原来五毛钱一盘的地主,这位又斗输了。赢了钱的喜形于色,买东西不还价,输了钱的难免沮丧。听说有人抽烟把打火机火苗调到只有黄豆那么大,因为他头天晚上输了钱,要厉行节约!十多年前,我神经衰弱,偏头疼,夜里经常睡不着,绝望地听着楼上的麻将牌哗哗哗一次次响起,时不时还有一块掉在地板上。有天实在忍不住,我挥拳打碎了一块窗玻璃。
冬夜漫长,人们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制造一点简单的快乐。听得最多的是一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前辈,聊六十年代末以来的风雨和恩怨。除了回顾历史,大家便相互戏谑,把对方出洋相的情形一遍遍地重现、放大。要不就是相互“占便宜”,以各种方式暗示跟对方的女眷有着特殊关系,其身份相当于对方的爹、姑父、姐夫、妹夫,甚至女婿。我好像没在其他地方见到过这种奇异的民俗。 如果有人起头,鬼怪故事也会轮番登场。此外,人们热衷于探索两性话题,充分运用隐喻、谐音等各种修辞手段,我认为完全有申报“非遗”的资质。盛家坝川鄂古盐道上的盐帮堪比沈从文笔下的水手,故事很精彩,小的时候听父辈讲过一些片段,很想听有人再讲一讲,可惜能讲这些故事的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陆续都不在人世了。
在这样的地方待久了,再古板的人也可能变得油嘴滑舌。老D是快退休的男同事,瘦瘦高高。小H是三十来岁的女同事,肥硕豪放。有一次,为了论证“脚杆”和“腿”的差别,我举例说,老D的那个叫“脚杆”,小H那个叫“腿”。这个话被小H知道了,对我怀恨在心,女人再豪放还是女人哪。
小镇上的居民淳朴、认命、坚忍、达观,身上闪耀着世俗的光辉。是啊,谁不想过好日子?但得慢慢来。
P6-8
展开